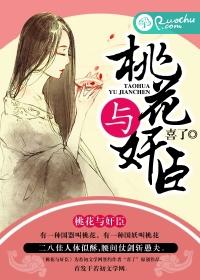BL小说>你手中的红线 > 第 32 章(第1页)
第 32 章(第1页)
晓志大病一场。
好几日,他高烧不退,烧得神智模糊。
宋彦泽没有联系他。没有信息,没有电话。
直到十天后的一个夜里,他被手机的震动从睡梦中惊醒。
他悄悄跑出阳台,诚惶诚恐地接起电话。
不会是DV带的事,被发现了吧?
“庆功宴都不来?不给我面子是吧?”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醉意。
他支支吾吾地解释,生病了、课业重、有好多书还没看完……等回过神,电话那头已传来嘟嘟的忙音。
他甚至没来得及告诉对方,庆功宴的事,根本没人通知他。
他不敢再提分手。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宋彦泽就会彻底忘了他,这段莫名其妙开始的感情,也就可以画上句号。
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已一只脚站在悬崖边缘,摇摇欲坠。
有一天,他在食堂看见了宋彦泽。那人身边站着个明艳动人的女孩,他们谈笑风生,很亲昵的样子。他只望了一眼,便一口饭也吃不下,几乎是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第二天,他还是没忍住去了图书馆,翻出当月的报纸。宋彦泽的纪录片获得了当地一家知名媒体举办的青年导演奖,报纸上刊登了对他的专访。
整篇采访里,宋彦泽提到了许多人,老师、朋友、同学……却唯独没有他。
他用指尖轻轻抚过报纸上那张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宋彦泽站在艺术学院的牌匾前,西装笔挺,眉眼含笑,依旧是那么帅气,那么耀眼。
为什么先提分手的是他,最后痛彻心扉的也是他?
“我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会喜欢呢?”
一次又一次,他在心里拷问自己。
他这样的人,平庸、怯懦、一无是处——有什么值得被喜欢呢?
“还好吗?”
吾名的声音将修理从自我怀疑的沉沦中唤醒。他抬起眼,对上那双清亮的眸子。
“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停下。”吾名伸手替他拂开额前汗湿的碎发,“休息一会儿也没关系的。”
疲惫沉甸甸的,像铅块,坠在身体里。仿佛一刻也未合眼地连续上了72小时的班,修理觉得自己的脸色此时一定难看至极。当看清吾名下巴上新长出的青茬和眼底同样浮动的倦色时,他蓦地心头一紧。
“你也会受到这些记忆的影响?”
吾名淡淡一笑,不置可否:“以我对你的了解,不一口气跑到终点,你是不会停下的,对吗?”
修理勾勾唇,心中郁结之气似乎顿时散了大半。是啊,他不会停下,一定会固执地跑到终点,但若没有吾名并肩同行,这段路途该有多么难熬?
“接下来的路,会更难走。”吾名敛去笑容,轻声说。
望进那双沉静的眼睛,修理没有说话,只是更加用力地握紧了对方的手。
前方不远处,忽然出现一道人影。修理定睛一瞧——那不是七年前的自己吗?
年轻的自己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手里拿着礼品盒,正站在男生宿舍楼下的宣传栏边,似乎在等什么人。
修理记得很清楚,那天是2007年12月28日。
临近期末,课业繁重,加上那段时间母亲的病情有些反复,他每周五一上完课便往两百多公里外的老家赶,忙得脚不沾地。元旦放假三天,他特意多请了两天假,回去陪母亲做检查。
离校前,他约晓志见了一面。
晓志的生日再好记不过,12月31日,每年的最后一天。
因为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生日,修理想着要送晓志一份特别的礼物。他特意挑选了一支钢笔,刻上了晓志最爱的那句电影台词——“Seizethe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