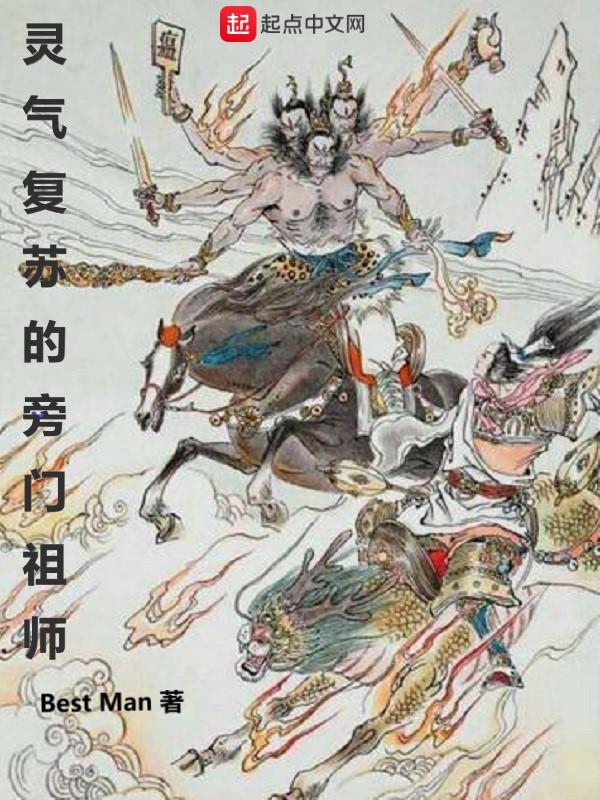BL小说>如风二十载 > 6070(第4页)
6070(第4页)
走出大楼时,天空的飘雪变大了。
凌晨的街道寂静又空旷,偶尔有车疾驰而过,又被雪花模糊成薄薄的剪影。
“顾兄。”
一道声音穿过风声与雪声,落在你的耳边,温醇如明月映水。
你闭上眼睛,脚步顿住,无声地叹了口气。
这一年多来,你把过去的记忆分组打包,分门别类地上锁,渐渐地不再想起。你的大脑生出了自我防御机制,将那些会让你疼痛的记忆一一隔绝。
可是,既然是锁,便会有钥匙。
随着那两个字穿过风雪落在你耳边,有关江湖的记忆抽屉被打开,繁杂的记忆如同奇点爆发一般,迅猛如洪地向你涌来。
你记起了一切。
涪江畔的偶遇;71年茅台酒;第一次去诊所看病;你砸在他昂贵西装裤上的滚烫眼泪;他隔着门缝为丢三落四的你递来海绵宝宝内裤;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唤鱼池的传说……
他为你揉按肚子时温热的手;被掌心捂热的暖贴;同吃的一碗面,上面飘着青翠的小白菜;你对他念的诗;他在看的星星;你梦里的银河。
愿卿久安,天边再会。
脚步声从身后来到身前,风雪中,他站在了你的面前。
他说:“一别三年,有幸再会,顾兄可安好?”
有冰凉的雪花融化在你睫毛上,你缓慢地眨了眨眼,望着他微笑的眼睛,鼻腔骤然涌起一股酸意。
你移开目光,称呼他:“谢总。”
“为何如此生分。”他说,“顾兄不记得我了么。”
你说:“刚才吃饭时,谢谢你帮我喝酒。天色不早,谢总又喝了许多酒,早些回家休息吧。”
你说:“再见。”
你转身离去。
一声轻微的叹息散在你的耳边,他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这是我有史以来吃得最为不安的一顿饭。从头至尾都在反复揣摩,我是不是惹你不开心了,所以你不愿和我相认。”
你背对着他顿住脚步,闭了闭眼,喉口一片干涩。
你能说什么呢,你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与他把酒言欢、夜雨对床、共谈理想的顾兄了。
江湖已经被深埋入湖底。
江湖人,应坦诚,应豪爽,应一笑震春秋。可如今的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坦诚的东西,你的记忆玫瑰凋零成土。你麻木不堪又虚度光阴。
你看似学会了很多东西,积极努力地生活。你学了一手好厨艺,精通电脑组装,甚至对莳花养草颇有心得。可当打游戏至夜深,当你坐在面团前发呆半个小时等待“室温发酵”,当你花一个下午为盆栽修枝剪叶……每当这些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多堕落,你在时光的长河中,毫无愧疚地挥霍着光阴。
你早已不是那晚的酒店里,一遍遍对他念“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顾如风了。
那时的你会心碎,会哭,会说真心话,相信梦想,相信远方,相信“于法不说断灭相”。
可现在的你,只剩冷冰冰的铁石心肠。
你能说什么呢。
……你还能说什么呢?
“抱歉。”你背对着他轻声道,风雪很大,但你相信他能听见。
“有顾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的声音沉稳带笑,“这说明顾兄并没有忘记我,对吗?”
你转过身来,又说了一遍:“抱歉。”
你说:“谢总,忘了那晚吧。”
你再次转身离去,并决定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会再停下。
“那晚后的第二天,我在南京老家院子里埋了一坛酒,黄泥塑封,软笔题字,取名‘见君子’。”他的声音夹着风雪传来。
你继续往前走去。
“我带着它一起来到了天边,将它埋在了现在的住所。今天山水相逢,既见君子,不知能否有幸,请顾兄一同品饮。”
你身侧的手捏紧了衣角,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加快脚步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