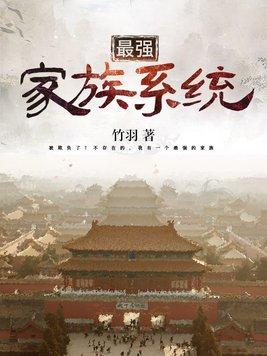BL小说>我不为妻 > 5060(第8页)
5060(第8页)
稍微冷静一点后,今夜之事就像是一根线,终于把?沈兰宜前世今生?不能理解的地方串联起?来了。
如果说,这辈子谭清让对她不假辞色,是因为她“自作主张”、与他相悖的主意太多,那前世,她安安心心地做着他的内宅妇,他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她表现出如此鲜明的不满呢?
谭清让没有喜欢她的理由,同样的,她似乎也不该有值得他刁难、刻薄的理由。
细碎的记忆在眼前不断闪过,沈兰宜恍然想?起?前世的一场家?宴。
宴席么,听起?来不过是吃顿饭的事情?,实际上那时谭家?已经渐渐起?复,说是家?宴,但实际上邀来的人不少?。
那时她还在许氏手下做着白工,为着这场给谭清让牵线搭桥的宴席,忙前忙后了许久,到开宴那日晚上,积攒的疲惫渐渐涌了上来,左右席间她的戏份不多,打过照面后,她没回自己屋子,就近找了间厢房小憩。
这样,即使席上有什么事情?来找,也不至于找不着她人在哪儿。
谁料她太累了,睁眼时已至天黑。
耳畔一点声息都没有,想?来席面上收都收拾完了,沈兰宜悚然一惊,猛地坐起?,却正好对上黑暗中漂浮着的一双眼睛。
榻尾矮几?上,谭清让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门?窗紧闭,就这么看?着她。
沈兰宜以为被?揪住了惫懒的错处,开口?说话时底气都不足,“三?郎……”
而谭清让久久未言。
沉默的交锋过后,最后,他只对她说了一句,回去。
沈兰宜不明就里地回了院子,翌日听闻,行五的那位郎君宴席上吃醉了酒,摔断腿要将养,她也没深想?如何。
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了,但是事情?的来龙去脉,今生?的沈兰宜倒也还记得。
她握了握拳头,两辈子的气堵在心口?,更愤怒了。
谭清让真?不是个?东西。
你弟弟对你的妻子心怀不轨,倒成了你妻子的错了?反倒让你有借口?疏远、刁难她?
谭清甫更不必说,上辈子是个?孬的,这辈子也不能转了性了。
这么看?来他的不轨之心早有预兆,前世那一遭是正好被?谭清让发觉;这一世她早早熄了在谭家?蹉跎的心思,反倒更催化了他那些不伦的念头,以为这便是可趁之机。
她那五弟妹对她莫名的敌意,如今也可以解释了。毕竟,谭清甫心里想?什么,外人尽未可知,可他的枕边人,却多多少?少?能知道一点。
捋清楚以后,沈兰宜反倒没了多少?意外。畸形的家?庭、刻板的权力关系,养出来的当然是这样的人,还指望生?出些好笋来吗?
她深吸一口?气,厌烦地退后两步,又朝地上晕得不省人事的那位道:“呸!有本事去把?你哥打瘸了去,朝女人使劲算什么东西。”
贺娘子也在谭府呆了一段时日,现下大概弄明白了来龙去脉。
她抬眉看?向沈兰宜,忽而又偏开了目光,轻声道:“我觉得,‘兄长’只是他的幌子。”
屋内,烛火并不通明,沈兰宜的鬓发也有些散乱,气恼的神情?于她的容色没有妨碍,反倒显得她更多了些人气。
她的容貌和她的性格一般,不显山不露水,叫人很难注意,平时也不会把?她和大美人之类的称谓想?到一起?,但若真?仔细去瞧,这份内敛沉静的美,与任何人相较却都不会逊色。
想?到谭清甫可能是见色起?意之后,沈兰宜心里一阵恶寒,只觉这种可能更恶心得让她无法接受。
她磨了磨牙,道:“我想?杀人。”
贺娘子的眼睛没再看?她,只盯着地上这位起?伏越来越不明显的胸口?,提醒:“杀人容易,灭口?却难。若死了,京兆尹查得到。”
沈兰宜只是嘴上说说,事实上,方才她之所以自己应对,而不是大呼小叫把?其他人喊来帮忙,与虚无缥缈的名声无关,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惊动?附近的其他人家?。
若闹得风摇影动?,只怕累及如今还未走脱的小郡主她们。
眼下更不可能生?事了,沈兰宜道:“贺娘子,你有什么办法把?他弄醒过来吗?”
贺娘子点头,又道:“先绑上。”
沈兰宜轻拍自己的脑门?,道:“对,先绑上,差点忘了。”
屋舍里有草绳,大概是原先住在这儿的人家?留下来编草鞋竹筐用的,沈兰宜取了一团来,捆猪似的把?谭清甫捆了个?严严实实。
贺娘子则取出一枚长针,扎入他颈间大穴。
医者仁心,然而此刻面前的不是病患,自然没什么温柔可言,下力又深又狠。
贺娘子淡漠道:“扎这里,阎王殿前也能拉回来一时三?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