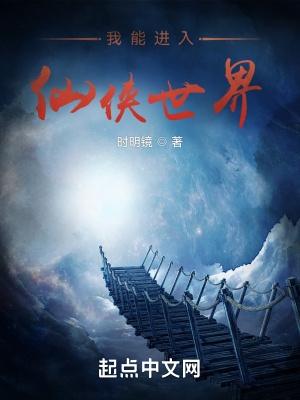BL小说>当县令的她跟叛国的奸臣好像啊 > 8084(第8页)
8084(第8页)
她一头散发,衣襟乱散,露出里面裹胸的隐秘,但全然没了平时的滴水不漏,仿佛失了视感一般,摸不到前路,惶恐扶着柱子?倒下。
周燕纾跪下,揽住了这人,任由对方的一头青丝无助洒满怀。
她感觉到了这人的颤抖跟痛苦。
一身的书香都?泛着药的苦味。
毒发,太痛。
但不及悔恨之事。
她听到这个人一如当?年在毒发后癫狂无助的呐喊。
“我没有错。”
“奶奶,我没有错”
————
明明没有什么都?没做错,也在步步抉择了最冷静的路,但偏偏次次结果都?让她悔恨不已?,仿佛次次都?错了。
那这就是命了。
周燕纾听到了外面的言洄急切的动静,也听到了他的不敢妄动。
更听到了怀里之人虚弱的喘息跟剧烈的颤抖。
她搂紧她,一如当?年差点跟明显暴露了震惊跟悔恨的陛下撕破脸的坚持,不要太医,不要任何人,她擅药,她可以救人,别人都?不行。
她要维护这个人的秘密跟尊严。
整个屋子?里只有她们?。
她没说?话,只是不断搂紧她。
直到奚玄渐渐清醒,能?看见东西,苍冷的手指如同湿漉漉,攥在周燕纾的手臂上?,知道她是谁后,一声的紧绷跟戒备都?如同笼子?里的小兽一般懈怠了。
她说?。
“我不是奚玄。”
这一句话,时隔多年,第二次对她说?。
“我知道,早知道。”
周燕纾低声说?,听到怀里人怅然又迷茫,痴痴的,“那我又是谁呢?”
是啊,她又是谁呢?
是多久多彻底的伪装,多不堪的过去,让她连自己的过去都?颠倒混乱了。
“不重要,你想要成为谁都?可以。”
“身份取决于地位。”
“已?经快过去了。”
奚玄,或者说?现在的罗非白低下头,听到外面在下雨,儋州百官还在这个府邸里。
她们?却介入了多年前帝国的秘事。
但过去了吗?
窗户,风吹雨打,竹影绿意斑驳憔悴,雨丝落在窗户上?。
是啊,下雨了,没有火了。
可是老太太走?的那天也下雨了。
又冷又热的,她这一生。
“怎么觉得每一天,都?那么漫长。”
她喃喃问。
“像极了那个老头子?每天都?在跪祠堂,他怎么熬下来的?”
周燕纾说?:“也可能?是跪太久了,起不来,所?以索性一直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