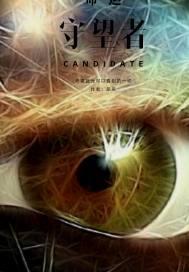BL小说>丞相大人御妻有道abo > 8090(第2页)
8090(第2页)
盛拾月闻言,先是松了?口气,又莫名愤愤不平,复杂情绪交织,就连她自个都想不清楚自己该如何抉择。
戴在手腕的翡翠镯子?敲在盛拾月指节上,微微泛疼。
宁清歌犹豫了?下,才道:“我母亲离世时……”
宁清歌眼?底的焦距散开,恍惚一瞬,
姜时宜的早逝,其实并不意外?,当年的姜家?何等耀眼?,她即是家?主女儿,又有不俗能力,向来?是被万人追捧的存在,即便之后被违背意愿嫁于宁家?,但也是个无比尊贵的宁相?夫人。
可?如今,天之骄女落入泥潭,被不起眼?的侍人蹉跎,只能依靠着?曾经辜负过的心上人,在宫中勉强存活,即便是性情再开朗宽厚的人,也难以开解自己。
更别说,姜时宜本身就是个气性不低的人,即便面上不显,心中也郁结难消,日夜难眠,再加上每天都要干活的缘故,姜时宜身子?一差再差,最?后一年甚至到时常咳血的地步。
只是她强撑着?病体,不肯告诉宁清歌和叶青梧,直到她离世时,两人翻查遗物时,才发现了?一堆染血的帕子?。
叶青梧当时呆愣许久,头一次不顾宫中的女儿,在掖庭之中、姜时宜房间里停留了?一整日。
她将?所有遗物都留给了?宁清歌,唯独那一箱染血的帕子?被她带走。
宁清歌闭上眼?,将?涌上来?的记忆强压下,只道:“我母亲离世时,叶姨曾吻过她嘴角。”
其实那都不可?以叫做一个吻,只是悲痛欲绝下的失控,以至于道德、教养、伦理?……
一切被曾经的叶青梧奉为圭臬的东西统统抛在脑后。
已站不稳的叶青梧跪在床边,紧紧拽住对方逐渐失温的手。
她一遍又一遍喊着?:“姜时宜别走、别走,我求你?,别走。”
“姜时宜……别离开我……”
她像年少?时趁着?夜深翻墙,跑到姜时宜门外?一样的央求着?,可?这一次却没有人从困倦中挣扎起身,为她打开房门。
“时宜姐姐……”
她最?后只附身,用酸涩潮湿的嘴唇贴在她冰凉唇角,像年少?曾幻想过千次万次的那样,轻轻喊了?声?:“姐姐。”
这是她们从年幼相?伴到之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最?大胆的触碰。
一人清醒,一人长眠。
清醒的人沉沦此刻,长眠的人永不得知。
姜时宜离世的第二年,叶青梧在姜时宜离开的冬日,重?病不治,撒手离去。
离世后,那一箱帕子?连同与姜时宜相?关的旧物,一并锁于她的棺椁之中,长埋地下。
“阿娘……”盛拾月张了?张嘴,嗓子?像被堵住一般,说不出其他的话。
她有些无措。
捏着?宁清歌手腕的手,不自觉地摩擦,在对方手腕留下淡淡的红印。
“阿娘……”她有些哽咽,分明得到些许宽慰,却又觉得遗憾,为她的阿娘感到不甘和委屈。
宁清歌叹息了?声?,贴过去些许,低头吻过盛拾月眼?角,将?咸涩的水雾抿去。
“宁望舒你?说,我是不是太笨了?、要是我早些知道、要是我早点察觉,我就、我会过去……”盛拾月口不择言,泛蓝的眼?眸被水雾浸透,便像是宝石一般盈盈破碎。
她还束着?对方的手腕,却不再像是束缚,更像是拉扯着?唯一的浮木。
宁清歌声?音温厚,沉声?宽慰道:“小九、这不是你?的错。”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阿娘吃了?那么多苦,我却什么都没有做,她那么疼我,”盛拾月听不进?对方的劝告。
她情绪崩溃,分明在静幽道长面前时,她还能强撑着?稳住心神,佯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地走回房间,甚至坚持到了?现在,直到宁清歌出现在她面前。
她语句颠倒,喃喃自语:“太自私了?我,什么用也没有,阿娘吃了?那么多苦、吃了?那么多苦她。”
“小九、小九,”宁清歌低声?唤着?她。
“都是因为我,阿娘装得好?辛苦、她本该和姜姨……”
她声?音颤抖,眼?眶红成一片,像只做错事的猫。
“小九!”宁清歌提高声?调。
“这不关你?的事,”宁清歌再一次重?复,偏头吻住她的唇,一字一句道:“不要钻牛角尖,这不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