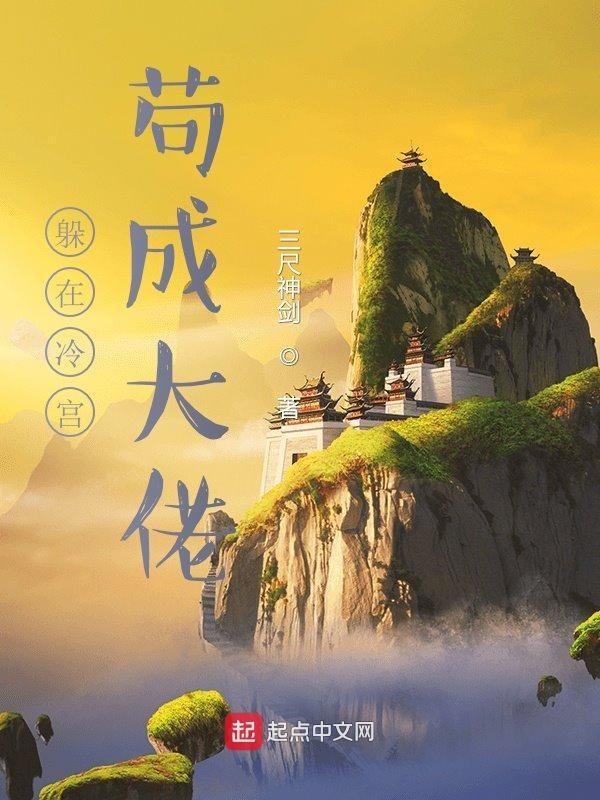BL小说>六丑 > 90100(第7页)
90100(第7页)
仪贞的片刻沉默并非拿大,而是惊讶忘言——若不细看眉眼口鼻,这哪还是她记忆里的懋兰姐姐?
“俞姐姐这话就是把我往外撵了。”她笑着上?前,自告奋勇地接过懋兰取下的背篓,险些没接住:“怎么这样沉?”
一笑一愣,依旧是旧时闺阁里的模样,懋兰的口吻不知不觉也就亲昵如昨了:“上?回雪爪路见不平,救了一只受伤的小野花狸,这是它?家长辈的谢礼,实在盛情难却,不然平日里,我也不摘这么些野果的。”
仪贞深以为奇:“雪爪?便是这小家伙吗?”呼哧呼哧在她们身边绕圈跑的小狗儿?便是遍身嫩黄、四个雪白爪子。她弯下腰,伸手欲去?摸它?,借以感知一二这山林间的异妙,诸如什?么野狸的酬答。
“就是它?。”懋兰忙不迭地让水栀将果子从背篓里捧出来,逗着雪爪往一边去?磨牙玩,省得它?对仪贞的裙裾跃跃欲试,“它?是这一片最热情好客的主人翁了,多少嘉宾都冲着它?,才赏光来我们这儿?一两回。”
二人说着话,懋兰让着仪贞往屋里坐,仪贞看了看旁边大树下的石桌石凳,说:“何不就在这儿?坐?大树底下好乘凉呢。”
懋兰闻言笑起来,又想起什?么,笑意更深一重,亦更渺远一重。依言拿一个坐褥来垫着,请仪贞在石凳上?坐了,自己挽了袖子浣过手,亲提了自摘自沏的忍冬茶来,斟了两盏,二人对坐细品。
春耕最要趁早,便是他们这一行样子货,亦不得不顺时随俗,故此忙忙碌碌到这光景,也才堪堪日近中天。
阳光尚和煦,头顶绿荫翠浓,仪贞微眯了眯眼,端的惬意,又偏首睇向懋兰,不无嗔意:“俞姐姐自谦村野,实则乃是世外高?士,这般闲云野鹤,我都无颜拿俗务来叨扰了。”
懋兰“嗯”一声,问:“是什?么事??我既敢与''娘娘''对坐对饮,难不成还拘泥于''雅''啊''俗''啊的吗?但讲无妨。”
仪贞便将亲蚕一事?道来,感慨道:“躬行兼诚心,好歹尽我所能吧。”
“唉!”懋兰脸上?浮现出一丝愁色:“才夸了海口,话音未落就要食言了——我这儿?并不养蚕,缘故你从前是知道的。若不介意,我倒识得几位养蚕的大娘,可以替你出面?说和,届时也可领你过去?,再?妥妥当当地接你回来,只要不进屋就好。”
“这也罢了。”仪贞说:“我观姐姐今时今日,好比脱胎换骨,一时就没想着,你仍旧怕蚕。”
“脱胎换骨,毕竟仍未换掉内里的魂魄啊。”树枝间斑驳的光影落在微垂的长睫上?,依稀是阁楼里那双被?菱花窗格阴影掩住的眼:“你方才谬赞我是世外高?士,其实我心有所羁,远未得超然——一是父母,二是…不过在此地偏安躲懒罢了。”
她的闭口不提里究竟有何人,仪贞多少有了底,来的路上?,她也确实打算过,但凡懋兰的口风里有丝毫余地,她必要为二哥哥竭力争取一番,可现下,她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月满则亏,人生在世,十全十美?也未见得是最得意的事?。纵有缺憾,但俯仰无愧,能这么活着就很难得了。”懋兰知道仪贞已?经懂她,重又释然,指了指头上?绿树:“这是枣儿?树,小满前后花开得满满当当,十里之外都是香的,那时你若来,必定喜欢。”
仪贞扬唇说“好”,慵懒地眺望四周,庄户里不种闲树,或桃或李,绯红洁白皆纷纷,蜂儿?蝶儿?闹嗡嗡的,是她读田园诗时畅想不到的天地人间。
第95章九十五
亲蚕礼在即,沐贵妃、武婕妤、苏婕妤皆来猗兰殿拜仪贞为师,练习采桑和缫丝染色。
“我?还没?见过蚕呢,听说是会咬人的,果真吗?”武婕妤瞄向了仪贞:“皇后娘娘,是不是该拿些?蚕来,让我?们观察一下习性…”
没?等仪贞开口,苏婕妤头一个不赞许:“眼下正是春蚕吐丝结茧的紧要关头,怎能拿来任我们摆弄,岂不作孽?”
“苏姐姐博览群书,我?却是不知者不怪嘛。”武婕妤有些?不服:“何苦说得这样罪大恶极?”
“苏婕妤说得?对,这些?小东西是蚕农们的生计,不是随便?拿来给我?们玩儿的。”仪贞一锤定了音,随即才转向武婕妤:“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届时若当真害怕,拿着银钩做做样子就是了,蚕只管吃桑叶,哪顾得?上咬人?”
皇后用金钩黄筐,妃嫔则用银钩,采来桑叶喂了蚕,待蚕结茧后,蚕妇便?选出好的蚕丝献给皇后,皇后再献给皇帝。
过后又择吉日,进行缫丝、染色等节。制成朱绿玄黄的衣料,以供祭祀礼服使用。
身为主祀者,真正?需要仪贞动手的流程其实?寥寥无几?,至于陪从的嫔妃,就更不必说了。
不过大伙儿的热情都很高,对于此?项劳作表现出了空前的翘首以盼。
在内织染局遣出的一行女染工中,仪贞还见到?了兼任赞者的燕十六。
内织染局的匠人们皆是从外头拣选出来的青壮年?男子,每年?领粮食银钱,随带入局的妻女亦多艺业精通,此?番仪礼上便?发?挥了作用;唯是这些?女眷们宫规方面?尚且生疏,掌印太监一事不烦二主,点了平日监工的燕十六前来照应。
仪贞见他来回奔走着,俨然?成竹在胸,心里替他高兴,预备着何时见了燕十二,也?在他面?前念一念,免得?他长日记挂。
旋即又觉得?不妥,回宫后招来燕妮儿:“上一次,你如何想起去皮影班的呢?”
燕妮儿而今生怕不能取信于人,竹筒倒豆儿一股脑地交代出来:“奴婢的干妹妹百灵儿,临行前把养的两只朱砂鱼托给了奴婢照料,奴婢把它?们放进了蔷薇馆外头的小池塘里,隔些?日子去看看,这才留心到?了那个养猫的内侍,实?在没?有别?的瓜葛了,奴婢不敢隐瞒,求娘娘明鉴!”
这话应当是真的,她自个儿也?该明白,再撒谎,猗兰殿就真容不得?她了。
不过仪贞不着急表明态度,甘棠在一旁听了,倒有些?忍不住:“你心里倒有成算。谁不知道蔷薇馆是娘娘从前住过的,你打着猗兰殿的名号,过去也?极便?宜,至于有没?有别?的勾当,却是无凭无据了。”
“娘娘…”燕妮儿这时才体会到?何为“一失足成千古恨”,简直百口莫辩——私养玩宠,本?就不是她能做的事儿,何况还是养在猗兰殿以外,隔三差五地出宫门,连个佐证的人都没?有。
仪贞叹道:“瞧,你又是为情义得?咎。我?这儿的人有些?爱好,我?一向并不禁止,只是因为有个朏朏,鱼确实?是不能养的,你那干妹妹可曾替你考虑过这一点?便?是她出宫匆忙,实?在周全不到?,你又曾来问过我?没?有?所幸而今无事发?生,你哑口无言,也?就罢了;倘真成了祸根,你又如何补救?补救不了呢?”
燕妮儿愧悔不已,一时竟泪水涟涟,伏地道:“奴婢糊涂,不是不知这些?道理,是困于他人的目光言语,宁可违背本?心行事,如今吃了苦头,后悔也?晚了!”
这番自剖实?属仪贞意?料之外,总算肯高看她一眼了:“孺子可教,便?不算晚。坐端行正?、毁誉由人,还有得?历练呢,不急于一时。”
燕妮儿蒙了大赦,新生一般,喜盈盈地去皮影班传过话,顺道看望蔷薇馆外的两尾鱼。
鱼儿活泼好动,放回池子里比养在小小缸中更是自在,无须她每常侍弄着。燕妮了却一桩事,越发?尽心地在仪贞身边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