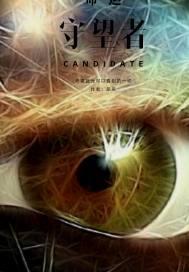BL小说>浪儿翻 > 140150(第2页)
140150(第2页)
没想到,先失足的是万琛。
龙可羡坐在书桌后,桌上摞着满当当的账本,临近年关,她忙着把北境和坎西城的军营账目做个分割,日后南北双营各论收支,这账才不会乱。
这几日她夜夜枕着算盘睡,梦里都在清账,因此听到尤副将报的话还有点儿诧异。
“你说什么?”
“王都有消息,朝中任命下来,最终给万琛定的不是吏部侍郎,也没有兼领东阁大学士!”
天色已晚,窗格里盛着橘红色的云浪,倏忽一团白影扑簌簌掠过,龙可羡陡然回神,问:“是哪里?”
***
“工部?”
万宅里,幕僚万河愁了一夜,嘴里长了个大燎泡,张嘴都疼,听见侍从问,只得闷闷点个头。
侍从脸色阵青阵白:“这可怎么好?老祖宗坐镇内阁,老爷又素有功绩,朝中上下均打点得当,不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吗?怎生……怎生……”
工部不吃香!
王庭势弱,骊王又以克己俭朴标榜自己,不会做那大兴土木的事儿,各地工事各地自就调度完了,工部这位置一直以来都不温不火,堪比冷宫。
内阁里现有的几位阁老,多是从吏部礼部户部升任的。
万琛本该升任三部之一的侍郎,兼领东阁大学士,待个一年半载,就能顺理成章迁任内阁次辅,这才算真正踏上了青云阶。
“原本折子都已经拟好了的,据查是都察院一封密奏直送中枢,定好的户部就成了工部。”
“哐当!”
万琛书房房门紧闭,里边突然传来碎瓷声,在夜色里荡出了涟漪,各房各院都熄了灯,不敢在这时候触万琛霉头。
书房外立着的几个幕僚面面相觑,正要敲门,那门忽然自内拉开了,万琛面色铁青:“六弟在哪儿?”
侍从立刻垂首道:“家主大人还在西九楼中,与琴疏先生论法。”
万琛在家中行二,但万家当家作主的不是他,也不是首辅大人万渠亭,而是他同胞弟弟,万壑松。
万家往上五代都是拿笔杆子的,名士大儒出了好几个,入朝为官的却是寥寥,万壑松少通神智,三岁作诗七岁写赋,十二岁作《抚水论》,被当时的定州巡抚采纳,此后六年定州都没有再遭过水患之灾。
万壑松有经世治国的才能,却不入仕,他为人十分低调,连文人之间的雅集诗会都不赴,二十二岁时成婚,然夫人早逝,只给他留了个女儿,之后十年都未曾续弦。
坊间有戏言,说万琛和万渠亭父子俩在任期间的几项功绩,都有万壑松在后边推动,因此万壑松有个戏称,叫做“帝师”。
行帝师之事,建安邦之功。
万琛连几个幕僚都没有召见,急匆匆地换了轿子,到西九楼的时候已经是深夜,竹楼门扉紧闭,他请书童代为通传。
书童打着哈欠,却告诉他:“家主大人已经歇下了,万大人明日再来吧。”
万琛在坎西城里就是土皇帝,谁都得卖他几分薄面,没想到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刻吃了闭门羹。
他不敢强闯,也没心思回府去睡,干脆撩了袍子,坐在这门槛儿上,和书童并排坐着等天亮。
书童揉揉眼:“万大人有心事吗?”
万琛烦得要命,半辈子的体面都在这一日焚成了灰,把他烧得面目狰狞,他粗声道:“是啊,到嘴的鸭子,飞了。”
书童却不以为然:“或许不合你口味呢,换道菜不好吗?”
“鸭子飞了,换你只小鹌鹑,你乐意吗?”万琛睨他。
书童点点头:“乐意啊,我个头小,鸭子吃不完,鹌鹑刚刚好,家主大人常常说,有多大的肚腹吃多少的粮食,撑破了胃肠就要吃苦头的。”
万琛喉咙梗塞,他不傻,这话就是点给他听的,万壑松摆明要他自咽苦果,但他不甘心,他十七当差,摸爬滚打二十载,才坐到这封疆大吏的位置,再往上够一丁点儿,就能踏上青云阶,叫他此时往冷宫里苦守三十载,他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万大人不坐啦?”书童站起来。
楼前的石灯吐出赤焰,松间小径光影缭乱,匆匆地吞噬了万琛的背影。
万宅,书房的灯火燃到天明,接连数日都没有息过人声。
万琛在坎西城里为官多年,攒下的门生故旧无数,肯为他发声的大小官吏很多,一时之间,关于万大人在位期间爱民如子的折子像雪花一样飞往王都,但都如雪落于海,没有激起半点水花。
万琛急了,他在这不同寻常的局势中嗅到了“弃子”的味道,他兵行险招,想要拉动更有话事权的北境王为他美言,却连三山军军营都进不去。 就在此时,刚刚乱起来的局面再度落进一颗石子,都察院二次进疏,参万琛私自篡改海务税数,以巨利向南域行贿。
这折子一上,顿时掀起滔天巨浪,连他老子万渠亭都压不住!拿士族的利益去喂那海上王,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