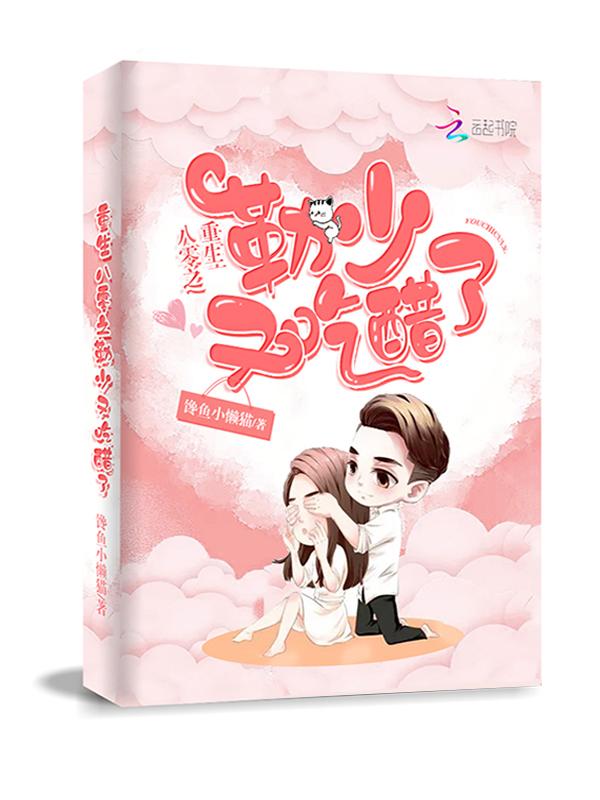BL小说>女摄政王 > 180200(第7页)
180200(第7页)
司徒清潇喃喃,“其实当日,皇姊已经提醒过我了,自古帝王多薄情,我当日说,我相信她。现在看来,倒真是我一厢情愿呢……都是我的错,是我轻信了她,才造成如此局面……”司徒清潇最后的话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融于了黑夜中。
自从走遍了大江南北,又经历了望月砂的事情,白蕤成长迅速,她眼睛水汪汪的,“姐姐,你不要这样了,不要再责怪自己了。洛儿他荒淫无道,德不配位,惹起百姓众怒。梁王不杀,百姓也会杀。梁王府里搜出来了遗书,刀尖上淬了剧毒,梁王是抱了一命换一命的决心去的,就算你那日去救他,他也活不成了,这是他的命数。至于圣上,她曾是一介翻云覆雨、炙手可热的权臣,怎么会是什么心软之人?身无官职的宗室远去幽州行宫,远离纷争,一生平安,得其善终,总比在这是非之地要好上许多,古来改朝换代,就算前朝宗室留得爵位在身,有几个能得善终的?”
白蕤越说越气急攻心,“这些宗室王爷、皇帝、太子,这些男子,做着府中家主,吃着国家的粮饷,一到外藩来犯,便把公主、郡主推出去和亲,美其名曰:这也是公主的责任。那他们呢?躲在女人裙摆底下茍且偷生么?当日将二公主推出去和亲的不是他们么?外藩来犯,这帮宗室王爷有一个人上阵杀敌么?如今这帮昏庸无道的人断送了江山,为何要你一个人肩负着?难道还要把这一切怪到你一个女子身上么?这些与你毫无干系,你何苦要责怪自己?女子要为自己而活,而非为了你的姓氏,姐姐!”
白蕤的母亲是盖世女侠,白蕤本就活得洒脱,她见不得司徒清潇禁锢自己,更见不得司徒清潇责怪自己。她见司徒清潇像是听进去了一些,爬上床榻双手扶着司徒清潇的肩膀,她的肩膀瘦得几乎硌手,“还有,姐姐,你忘了她吧。”
司徒清潇缓缓抬起头来,额角汗湿,有几缕发丝粘在脸上,如画的眼眸猩红,眼神怨恨、凄凉、悲怆,她紧紧攥着白蕤的袖子,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看向白蕤的目光都带着乞求,“这其实是一场梦,对么?”
白蕤只觉得陡然间一股酸涩涌上了喉头,顿时泪水便夺眶而出,“阿姊,求你了,不要这样好不好……求你了……”
她何曾见过这样狼狈不堪、亡魂失魄、心神失常的司徒清潇?
司徒清潇慢慢松开了紧抓着她袖口的手,无助地垂下了眼眸,长而密的睫毛投下了一片阴影,显得苍凉而孤独。
她看着一向端庄优雅的姐姐狼狈到几乎疯癫的模样,忽然惊觉,比起司徒清洛死在眼前的冲击,比起恨,她更多的是怨、是痛,是司徒云昭的不爱与抛弃。
白蕤只觉得,这一刻的司徒清潇,宛如一朵零落的高洁白牡丹落入尘泥里,沾满了鲜血与泥土,破碎而凄冷。
白蕤曾亲眼见过司徒云昭,她也想不明白司徒云昭为何会如此,难道真的人心易变么?望月砂是这样,司徒云昭更是这样。她又气又急,“阿姊,我去找她,我去敲登闻鼓,我还认识几个从六品的国子监丞女官,我求她们带我去面圣,我要去问她为何要这样对你!”
“不要去,不要去,蕤儿……”司徒清潇猛地抬起脸来,她容色凄美,睫毛濡湿,眼神里盛满破碎的凄凉,像是被打碎的瓷娃娃,任多么努力也拼接不起来。
“自古帝王多薄情,阿姊,你就放下她吧!阿姊,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看当初我发现望月砂的事情时,”白蕤说到这里,还是忍不住咬了咬唇,“如今我不也是好好的么,你也会好起来的,姐姐,相信我。”
话说出口,她又有些后悔了。因为那个名字脱口而出的时候,心的跳动还是有了变化。
自己当日,司徒清潇也是这样陪伴在自己身边,而自己常常流泪大哭宣泄,如今司徒清潇的状态显然比自己要严重许多。
白蕤不知道该怎样救她,只觉得,司徒清潇这样不流泪反而是一件坏事,于是劝慰,“姐姐,你若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
她明白,人在悲痛欲绝、痛苦至极的时候是哭不出来的,那种折磨的痛已经占据了所有,没有力气腾给悲伤流泪。只有当情绪撕开一个口子,宣泄出来,才会好得多。
司徒清潇将头埋在双膝间,青丝凌乱地散落t下来,可人却仿佛干涸的枯井,睁着眼睛,流不出一滴眼泪。
第185章后嗣
司徒云昭正站在龙案前,端详孟子衡从国库拿来的一把蟒弓,是当日晁京为了讨好司徒清洛进献而上的,弓身由玄铁打造,据说威力无比,不畏冰火,不畏刀枪。
一道沧桑沙哑的声音传来:“皇上好雅兴啊。”
司徒文敬虽则拄着拐杖,行动却不见迟缓,依旧行了礼,“老臣参见皇上。”
司徒云昭面色淡淡的,嘴上却很客气,“何须多礼。朕在赏弓,卿不妨试试?”
司徒文敬双手拄着拐,语气中却不见几分恭敬,“不了,臣这一把老骨头,拉不开弓喽。”
司徒云昭倒是听得出几分倚老卖老之意,“来人,赐座。”
司徒文敬坐了下来,虽则满脸皱纹,头发和胡须花白,但他目光锐利,声音洪亮如同古钟,丝毫不见老态。
司徒云昭略作关心,“朕登基以来事务繁忙,一直无暇宣召,司徒卿近来身子可好?”
“一切都好,多谢圣上关怀。老臣如今一个闲散官职在身,每日无所事事,得闲休息,自然好得不得了。”
任谁听不出话语中的阴阳怪气。孟子衡翻了个白眼,硬挤出了个笑容,转过身来,“桓王,许久不见。”
司徒文敬语气颇为讥讽:“哟,原来孟相也在,恕下官眼拙,方才不曾看到。下官早已不是什么桓王了,孟相可莫要乱叫。”司徒氏一干人皆被剥了爵位,但宗室中还有不少在朝担任官职之人,只要身有官职,无论能力高低,司徒云昭都给了这个面子,留用了。司徒文敬因为一直曾有银青光禄大夫的四品闲散官职在身,后司徒云昭登基,又给他抬为了三品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嫡子司徒清榕也有言官的官职在身,所以父子二人依旧住在原来的府邸,在朝中效劳。除了撤去了王爵待遇与王府牌匾,其余一应礼遇几乎未变。
孟子衡似乎倒也不生气,依旧笑嘻嘻地,“我一时口快,司徒大人莫计较。”
司徒文敬嗤笑了一声,上下打量了两眼孟子衡,又转开头目视前方,语调拉长,“对了,还未恭喜孟大人高升啊。”
“哪里,大人客气了。你我皆是为圣上效力,没有圣上英明和大人当日仗义执言,何来我今日富贵,现下朝野上下、满朝文武,何人不知司徒大人高风亮节、忠肝义胆、从龙有功。如今民间夸赞您老人家的文章都满天飞呢。”
孟子衡说的倒是实话。司徒文敬却不给他一个正眼,目视前方,也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下官老了,腿脚不便,就不起身给右相大人行礼了。”
“无妨,既是圣上赐座,大人自然不用起身。”
司徒云昭把玩间将弓拿了起来,对着前方,用了力拉开弓弦,作出平日拉弓射箭的姿势来,孟子衡在龙案一侧捧场,“哇,听说此弓拉开需要极大力量,圣上果真厉害!”
他一边捧场一边给司徒文敬介绍,“听说三百年前玄朝时期的赫连将军曾刺杀过蛟龙,这把弓上的弓弦便是蛟龙的龙筋所制作的。”
孟子衡话毕,司徒云昭突然间将弓调转了个方向,冲向了司徒文敬。
司徒文敬下意识地惊吓着后躲了一下,连手中的拐杖都瞬时握紧了,随即才反应过来这只是一把弓,压根没有箭,顿时挂不住了脸面,脸色铁青。司徒云昭将弓放了下来,弯了弯唇角,“可是吓着司徒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