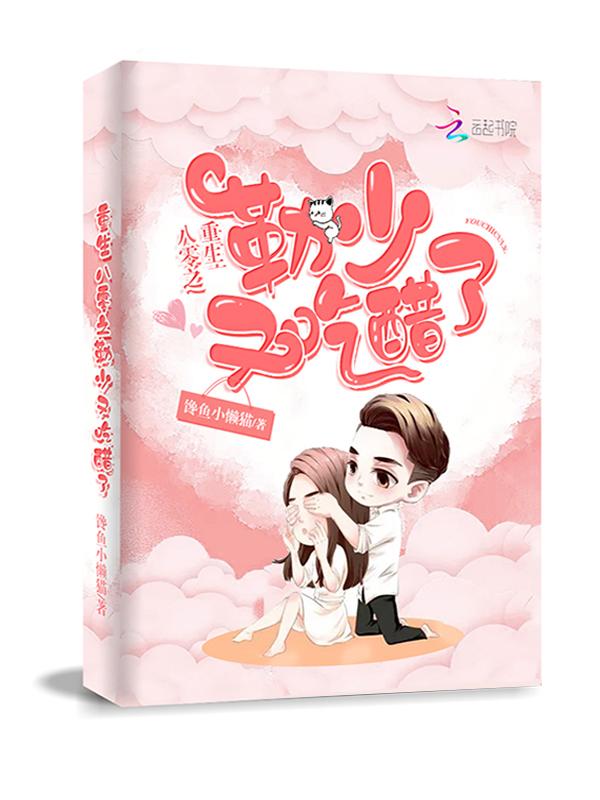BL小说>酒厂BOSS在追漫画 > 第228章 Extra(第3页)
第228章 Extra(第3页)
研究生结束后才轮到本科,念到他的名字之前,黑泽阵低低地俯在他耳边问:“你会走吗?”
唐沢裕不语。
于是他低沉地笑了一声。紧接着那只手就松开了,台上的校长朗读出他的名字,黑泽阵转过身,没有任何预兆的,自始至终牢牢紧牵的热度,忽然就这样轻轻放开。
唐沢裕的指节无意识弹动一下,空落落的指缝间蹭过了一缕风。
人群里银发的青年上台,鞠躬,微微向银发的校长示意。他双手接过了那证纸页,背过身时,台下的人影还在。
唐沢裕一直等到轮到黑泽阵发言致辞。他一向是学生中最出众瞩目的那一个,渐渐地人头攒动,人群嗡声交换暗语。几个竭力踮脚的人挤到他前面,唐沢裕这才后退半步,他压低帽檐,无声地转头向后离开。
——到这就可以了。
——这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颠倒的。荒谬的。
他逆着人群往后走去,脚步在起初不露声色,到边缘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两个黑风衣的人拦在前面,唐沢裕一眼将他们与普通的学生区分开。这是黑泽阵留下的人。他们零零散散地分布在草坪上,此刻却全都汇聚过来,不远不近的距离,恰好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唐沢裕在帽檐下扫视一眼,没有突围的可能性,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一场硬仗,他在口袋中轻轻地活动手腕——
被囚困的时间太久,他的身手应该是退步了,但要摆脱掉这些追兵并不难。
于是他径直往前走去,无视拦在前方的两个人,步履平稳的同时绷紧身形,微微调整了呼吸和行走的发力姿势。
他已经处于战备状态,而那个人走近的第一句话却是:“Gin先生有话留给你。”
“钟楼是最好的位点,”他说,“他还说,如果您继续从这里出去,走一步,他就开一枪。”
唐沢裕长久封冻的表情上,终于暌违地出现了结结实实的愕然。
他刹那间回过头,脚步就此僵在原处。最高的钟楼有一抹反光,这个角度,光亮恰恰好照在眼里,那是狙击镜反射的光亮。
一瞬间,广阔的校园、建筑,拥挤的人群与喧嚣,所有的似乎都不见了,世界短暂地陷入空白,只听见话筒里回响的毕业致辞,以及从高台上落下来,不偏不倚地注视着他的目光。
黑泽阵刻意点出钟楼,这一细节才最具威慑力。唐沢裕怎么不了解这里呢?他熟悉这座校园就如同黑泽阵。入校的第一天他就看到那里,他说,如果要俯瞰风景,这座钟楼就是最好的位置。
而如果要安置狙击手,……这里当然也拥有着最佳的视野。
走一步,他就杀一个人。
随着他脚步停住,围来的黑衣人步伐也停下。他们在人群中长久地缄默着,如同某种意义上的隔空互峙。但唐沢裕感觉不到这些。所有的感官里,只有一道视线最执着、最炙热,一切干扰都消失了,全世界只剩两个存在,唐沢裕背对着草坪边缘,而他身后,黑泽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时间在空白中过去很久。
沙沙的脚步从后方过来,带来青草被重量踩折的声音。银发的身影靠近,微微俯下身,想去牵他垂落在身侧的手。
唐沢裕猛地一甩。
——他从没有这么激烈的反应,整个人肉眼可见的抖了一下,他条件反射地用着力,黑泽阵的角度能看到他后颈,每一寸肌肉都是绷紧的。
唐沢裕的所有反应都无意识,想甩脱身后过来的那个人,可他失败了。黑泽阵只是被挥开两秒,紧接着,扣住手腕如灼热的铁钳,压倒性的、不可违逆的力道从上面传过来,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一下反抗,他的动作就被他牢牢控制在手心里。
“我很高兴。”
低沉的语气慢条斯理,他甚至用气音轻轻地笑了一声。
“你没离开。你还在这里……我很高兴。”
——明知道结果只会让自己失望,却始终难以自扼地一次次尝试与重蹈覆辙。几乎像某种强迫似的重复。
包围的黑衣人似乎在一瞬间消失了,世界只剩下两个人,黑泽阵紧攥着他的手。
他以近乎和缓的语调说:“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