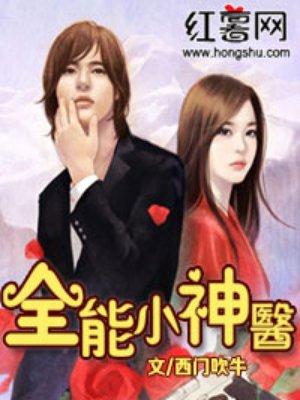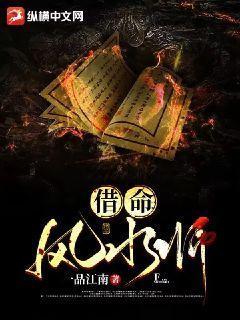BL小说>捡个姑娘当外室以后 > 第182章(第2页)
第182章(第2页)
四年前与她和离,便是他押上算筹,赌得最大的一场。
今上动了心思,西南偏远之地,一去便是几年,他不得不走,可秦霁不必。
她好不容易才回来,不会为了他走,可就这么俄延在京城等他,也很没有道理。
那时秦霁心中本来就没有他,再独留在这儿,岂非让他们之间平白生怨?
她或许不会,但旁人定会加诸口舌。只要有那么丁点生怨的可能,都会让陆迢极其不安心。
他想要她没有顾忌,不受旁的干扰,好好在京城过和以前一样的日子,再——偶尔想起他。
最后一条实在太难,他唯有在放她走的时候干脆利落些,忍下所有要问的话,叫她记得这一点好。
陆迢的赢面实在太小。
在西南带兵,空下来的时候,将士们都在各处找人写家书。他也写了,只是一封半封地写下去,怎么都是词不达意,言不由衷。
那些信是怎么都不能寄给她的,一寄过去,他就要在秦霁面前原形毕露。只能写一封,留一封。
陆迢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想她,对着那些信,却找不出一个寄出的理由。
若是她在京城有了别人呢?李思言虽然能被他提前支走,可京城里的豺狼虎豹,何止那一只?若是没人能拦下,又该如何?
陆迢不知道,只能少想一些,再少想一些。
直到那日拆开来信,他得知自己有了个女儿。
恍然不止有了给她寄信的理由,还有了去看她的理由。
到后来,秦霁一点点朝他走近,她走的又慢,又小,他看在眼里,却只能站在原地等。
至少要等到她先认清她自己的心思,不再摇摆,不然那些凭空耗掉的时日便会毫无意义。
因着这些种种,他才不愿告诉秦霁。
不愿告诉她,他胸口新添的疤,是她的亲爹爹,他的岳父大人伤的。
不愿告诉她,这几年,他一直在让人留心照看她金陵的师父师母。
陆迢这次不要秦霁因为旁的事情心软动摇。
他要她明明白白,坦坦荡荡地喜欢他。哪怕这喜欢只有一点,尚且不及他的一半。
只要有就行了,陆迢想。
这次,他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