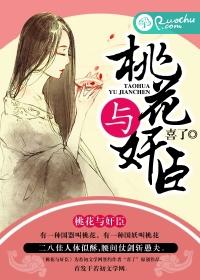BL小说>绿爱之高贵美艳的丝袜舞蹈老师妈妈 > 第112章(第2页)
第112章(第2页)
月光漫过她一字高跟鞋里颤栗的足尖,照亮宝石蓝丝袜大腿根处被啃咬出的红痕,尼龙纤维翻卷的边缘挂着晶亮涎丝,宛如毒蜘蛛精心布置的捕猎陷阱,在黄福勇的拇指完全埋入禁忌之地时,妈妈哀嚎出声:“会…会坏的……”
黄福勇突然发力撞向宫颈,他强迫妈妈扭头看窗帘,帘纱中半露的玻璃倒映着蜜桃臀正随着抽插频率泛起绸缎流动的诡光,剧烈收缩的肠道和蜜穴带来双重快感,妈妈喉间溢出的娇艳卷着十分讨好:“咿咿咿?……好哥哥……亲丈夫……那里……真的不要……饶了淑婉嘛……”江南女子特有的吴侬软语尾音,将端庄人妻最后一丝矜持揉碎成床单上的水渍。
“啵……”
黄福勇突兀的抽出肉棒,他拽起蜜臀,将妈妈修长的宝石蓝丝腿扳成芭蕾舞者谢幕的弧度,随着黄福勇掌心的茧子碾过她腰窝,蜜桃臀在老汉推车姿势下晃出山竹的果肉纹路,在龟头抵住菊穴的瞬间,妈妈散落青丝摇荡成拨浪鼓,“不………不要………会……会裂开的……”
“放松宝贝,您这后庭花可比骚逼还馋人……”黄福勇嘴角勾起坏笑,食指蘸取蜜穴溢出的晶亮涂抹菊蕾。
妈妈紧咬的唇瓣在情欲蒸腾中晕染成带血的罂粟,眉梢忽皱成破碎的远峰,颤抖的尾音裹挟惊惶,“啊嗯……别……齁齁齁……会……会痛死的……”
待那根狰狞肉棒抵住后庭微微进入一分的刹那,妈妈心底涌起一股强烈的恐惧,一想到即将被硕大的肉棒撑开,塑形成它的形状,腰肢本能地向前轻颤。
黄福勇俯身将胸膛压上她蝴蝶骨的凹陷,鼻尖深埋她汗湿的颈窝,犬齿叼住耳垂轻扯:“宝贝儿这朵雏菊……很害羞呢?!”灼热的喘息裹着雄腥味灌入耳蜗,下身浸透的汗渍在她腰窝烙下深褐色荆棘纹。
那双粗糙的大手随即固定住妈妈不堪一握的纤腰,掌心热度透过薄薄丝袜传递过来,当紫红龟头蛮横顶开紧闭菊蕾间,妈妈染着薄汗的指尖骤然抠进床单,散落的两缕青丝,沾着唇釉的碎发粘在汗津津的腮边,像被暴雨打湿的花鸟残卷。
“啊……等……等……”泣音像化不开的蜜针,妈妈足尖在床沿蹭出道德崩裂的纹路,黄福勇指腹碾过她腰窝未褪的红痕,掌纹陷进缎面油光丝袜包裹的蜜桃臀时,宝石蓝丝线绷紧的嘶响混着肛口括约肌撕裂的黏腻水声,在寂静月夜里织成撒旦吟唱的乐章。
“夹这么紧是想把老公鸡巴夹断?”黄福勇獠牙掠过妈妈滑腻的背脊,新鲜齿痕叠在旧伤上宛如倒诵《圣经》的齿间血沫,他腰胯猛然发力,整根紫红肉棒在晶亮肠液润滑下长驱直入,龟头棱角刮擦直肠褶皱的触感令妈妈悲泣哀吟,“要……要裂成两半了……”
雪乳在撞击中晃出粉白的潮红,乳尖渗出的汗珠沿着昨夜齿痕蜿蜒,在小腹拖曳出泥泞轨迹,妈妈屈指拭去眼角将坠的泪珠,深紫色甲油在月光下泛着带毒的紫晶光泽“轻……轻些……老公……求你……”哀求弥漫着春情黏连,月光映出两人交缠的剪影。
后庭被彻底撑开的胀痛混着隐秘快感,在肠壁褶皱间酿成腐蚀理智的催魂散,裆部裂口边缘翻卷的尼龙丝线,那里正勾着几缕混合汗液的浊白黏液,妈妈染着血珠的嘴角突然扬起破碎的媚笑,指尖婚戒随着摆臀迎送的动作晃出堕落的银涟:“齁噢噢噢?……坏人……亲哥哥……疼……那里……要被你的……臭鸡巴……捅穿了……”尾音卷着化雪的甜腥,柔黄向后探去,指尖在黄福勇小腹刻下带血的月牙。
“疼就掐我……”黄福勇牵引她玉手按在自己大腿虬结肌肉,另只手突然探向湿漉漉的蜜穴,温柔揉捏起充血的花蒂,“一下喂两张嘴!”
“啊……太……太犯规了老公……齁噢噢……淑婉要被你玩死了……”妈妈指尖深掐进他腿肉,菊穴括约肌随着蜜穴快感映射剧烈收缩,绞得黄福勇眼白泛红,全身青筋暴起如老树虬根。
月光漫过她因疼痛扭曲的绝美容颜,原本端庄娴静的妆容此刻被晕染成雨打海棠,黄福勇喘着粗气放缓顶送节奏,犬齿厮磨着她后颈卷走摇摇欲坠的汗珠:“嘶……放松些……对……就这样……”
“啊……咿咿咿?……老公……好奇怪……又疼……又麻……淑婉要疯掉了……”妈妈哭腔的娇吟柔的黄福勇骤然粗喘,散落的青丝随抽插缠住黄福勇麦色腕间,当菊穴逐渐适应异物侵入,她绷紧的腰肢又缓缓塌陷成受难圣母像的弧度,雌香溢散的丝袜足尖开始无意识摩挲他小腿汗毛。
黄福勇趁机拍打她晃荡的丝袜蜜臀,揉捏花蒂的指腹突然三只并拢刺入蜜穴:“宝贝这里边开始吸我了……”感受到肠壁蠕动的吮吸,紫红肉棒猛然贯穿深处,“还说不要?嗯?”
“啊……死了……齁齁齁噢噢?……要死了……骚逼和……菊穴……都被老公塞满了……咿咿咿……啊……又要喷出来了……”淫靡的呻吟酥麻入骨,菊穴深处传来的饱胀感让妈妈慌了神,蜜穴却诚实地涌出大股汁液,顺着丝袜裂口浸湿渗入菊穴。
“啊哈……好人……齁齁齁齁……慢……慢些……真的挨不住了……淑婉……舒服的要昏厥过去了……”甜腻勾人的浪叫销魂入骨,睫羽垂落的阴影里藏着未尽的讨饶和媚意,菊穴开始贪婪地吞吐着粗长肉棒,“嗯……坏老公……淑婉……咿咿咿……早晚死你手里…啊……太爽了……”
“那敢情好……”黄福勇獠牙撕咬她颤动的耳垂,肉棒在肠壁深处剐蹭出噗嗤沙响,“今天就把你肏……死~”
未尽的话语被妈妈骤然收缩的菊穴和花心媚肉悉数绞碎,激的黄福勇胯骨肏出铁匠淬火的重击,黄福勇俯身死死掐住她晃动的乳浪,指缝溢出的乳肉泛着隔夜凝脂的柔腻。
“啊……丢……丢了……咿咿咿……骚逼的水水……和菊穴……都要丢出来了……啊……齁噢噢噢?……老公……福勇老公……淑婉的亲丈夫……”
妈妈裹着宝石蓝缎面丝袜的足弓骤然绷紧,美腿渗出细密汗珠将丝袜黏在肌肤凝成粉红,精巧的锁骨随痉挛起伏成振翅欲飞的蝶,雪腻沟壑在剧烈喘息间晃出昼光倾洒贝加尔湖的粼波。
“要……要融化了……里面……齁齁齁噢噢……烧起来了……淑婉……又丢给……老公的臭鸡巴了……”破碎的呻吟裹着濒死的崩溃,蜜穴媚肉吮住绞紧黄福勇手指,肛门肠壁在肉棒抽插下颤巍巍的泌出丝缕淫靡油脂,晶亮潮吹液纠缠着溢出的油脂顺着会阴处喷涌,在折叠床单绘出富士山雪顶消融的纹路。
黄福勇见妈妈喷的千娇百媚的浪态,喉间滚出低吼,原本攥住晃动的雪乳暴戾捏成淫靡形状,紫红肉棒在菊穴肠壁剐蹭白腻油脂,突然抵住前列腺腺体疯狂震颤。
妈妈痉挛发颤的娇躯溢出雌香,绷直的足尖突然勾起脱落的一字高跟,鞋跟敲击钢架迸发的脆响混着求饶:“啊咿咿咿!?……满……满进来了……要装不下……臭鸡巴的浓精了?……啊……齁齁齁……坏人……亲老公……”
精囊收缩的瞬间,黄福勇獠牙滚出灼息,连绵不绝的浓精如同熔化的铂金灌入直肠褶皱,烫得妈妈灵魂撕裂,指甲在黄福勇大腿抓出崩溃的血丝:“淑婉……咿咿咿?……要被……老公臭鸡巴的浓精……灌成泄欲人偶了……”泣音泄出天鹅垂死般的哀艳。
月光将两人重叠的剪影拓在窗纱,摇曳成连理枝绞杀刑架的死囚……妈妈染着浊液的中指突然探入自己尚在痉挛的蜜穴,搅动出黏腻水声作为这场背德盛宴的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