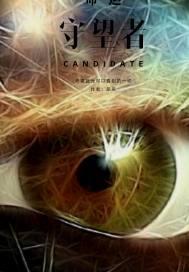BL小说>娇妻人设也能爆改龙傲天吗 > 329晋江文学城首发(第2页)
329晋江文学城首发(第2页)
没有人指责,没有人打断。她们只是听着,流泪,然后轻轻抱住身边的人。
第三日清晨,村长带着族老前来兴师问罪,却发现祠堂大门已被拆下,架成了临时讲台。台上站着那位刻字的农妇,手里捧着一本皱巴巴的《心莲誓》,身后是百余名手持蜡烛的妇女。
“我们不是造反。”她说,“我们只是不想再装傻了。”
与此同时,漠北紫莲丛中的“启言之花”持续释放波动,与看要自的血莲印记共鸣愈强。某夜,她在冥想中突然进入一片奇异空间??不再是灰白废墟,而是一片无垠花海,紫色莲瓣随风起伏,每一朵都映出一张女人的脸:有年轻的,有苍老的,有含笑的,有哭泣的,却都静静望着她,仿佛等待某种召唤。
一个稚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要不要回来?”
她转身,看见那个曾在数据废墟中出现的无面小女孩,此刻脸上仍无五官,但身形已长大几分。
“你是谁?”看要自问。
“我是你们遗忘的名字。”小女孩轻声道,“我是第一个被抹去记忆的人,也是最后一个不肯闭眼的影子。她们烧了我的碑,泼了我的名,可只要还有人做梦,我就不会消失。”
“你想做什么?”
“我想回家。”小女孩伸出手,“但我知道,真正的家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所以我来找你??因为你既不忘伤,也不恋痛。你能带着她们往前走。”
话音落下,花海骤然翻涌,万千紫莲同时绽放,花瓣飘向天际,化作点点星光。看要自感到一股浩瀚的情绪流涌入体内??不是命令,不是控制,而是一种深沉的托付:**请继续说下去,哪怕声音微弱。**
她猛然惊醒,额间血莲灼热如烫。苏砚守在一旁,神色紧张:“你消失了整整三个时辰。共感网络显示,北方十七个觉醒节点同时激活,持续共振达四十九分钟。”
看要自坐起身,呼吸微颤:“不是我消失了。是我被接引了。”
她将梦境复述一遍,末了低声道:“那孩子不是敌人。她是驯心堂最初的灵魂残片,是所有被剥夺话语权者的集体意识投影。她不是要复活旧秩序,而是想完成未竟之事??让每一个‘我’都能真正发声。”
苏砚久久无言,终是叹道:“所以我们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段历史的回声。”
“那就让它听见我们的回答。”看要自起身穿衣,“我要去漠北。亲自采下那朵花。”
“太危险!”苏砚急道,“朝廷已在沿途设卡,追查‘妖花惑众’之案。且那片区域地脉紊乱,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精神崩解!”
“正因如此,我才必须去。”她望向窗外渐明的天色,“有些路,只能由走过最深黑暗的人去走。况且……”她嘴角微扬,“我不是一个人。”
三日后,一支由十名资深学员组成的护送队悄然出发,伪装成采药商帮,携带着特制的地脉稳定仪与加密通讯器。临行前,阿穗拉着看要自的衣袖,递上一幅新画:一个小人站在雪山之巅,手中高举一朵紫莲,光芒洒向大地。
“你一定要回来。”小女孩仰头说,“等你回来,我就学会写‘希望’了。”
看要自揉了揉她的发:“等我回来,咱们一起教全院的孩子游泳。”
队伍穿行于风雪之间,历时十七日抵达漠北。紫莲丛位于一处古老祭坛遗址中央,四周散落着断裂的石碑,依稀可见“顺心”、“守默”等字样。而那朵启言之花,孤傲挺立于寒风之中,花瓣流转金纹,香气无形却直透魂魄。
看要自缓步上前,双手合十,轻声道:“我不是来占有你,是来聆听你。”
她伸手触碰花瓣的刹那,整片花海轰然震动,地脉巡仪警报尖鸣,天空裂开一道极光般的缝隙。她的意识再度被拉入共感空间,这一次,无数声音交织响起:
>“我叫林婉娘,死于贞节牌坊建成那夜。”
>“我是陈九姑,被灌药三年,只为学会微笑。”
>“我是沈小娥,十三岁那年,亲手烧掉了自己的诗稿。”
>……
她们不是控诉,只是陈述。不是复仇,只是存在。
看要自跪倒在地,泪水滑落:“我听见了。我都记下了。”
就在这一刻,启言之花缓缓脱离茎秆,自动落入她掌心,随即化为一道紫金流光,融入她眉心血莲印记。刹那间,她的视野豁然开阔??她能感知千里之外某个女孩正在第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能听见深宅中一位老妇在梦中喃喃“我不想死得像个影子”;甚至能察觉到京城书院里,一名少女正悄悄撕掉“礼法守则”,在背面写下“我要恋爱”。
她回来了。不只是她,是所有被埋葬的声音,都找到了归途。
归程途中,消息如野火蔓延。各地游学队纷纷反馈:觉醒频率提升三倍,自发组织的“姐妹会”新增四十余处,更有男子开始主动学习共感基础课程,称“不想再做聋子”。
而京城书院内,那名撕纸条的少女被罚跪三日,却在放饭时悄悄将一张字条塞给送餐仆妇。仆妇识字不多,辗转找到守心院联络点,展开一看,лишь八个字:
>**“你们赢了。我在学说‘我’。”**
看要自读罢,久久伫立莲池畔。冬雪已融,春意初萌,新一批孩子正在院中练习手语,笑声清脆。
苏砚走来,低声问:“接下来呢?”
她望着池中倒影,轻轻道:“继续教她们游泳。不是为了逃离这片水,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
**这水,本就属于想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