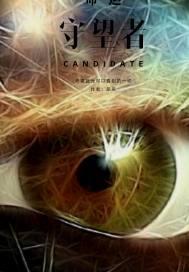BL小说>浮光弄色 > 第25章 影落沈图旧案重启(第2页)
第25章 影落沈图旧案重启(第2页)
我低语:“这是猎魂之局。那些孩子,是祭引之引。而门——”
“——才是真正的凶器。”唐蔓道。
堂中一时静默。
火炉中松柴爆响一声,烘出一股热浪,却驱不散心头的寒意。
“你怀疑什么人?”我轻问。
唐蔓摇头:“现在没人。我只知,有人在开门……而我们,得在那门彻底打开前,将它封死。”
我指尖在那拓印纸上停了片刻,忽然抬头,语声缓慢却坚定:
“这个孩子,我想亲自看看。”
唐蔓眉尖一挑,似早有预料,淡淡应道:“你曾习过岐黄之术,我也正想问你——可愿随我一趟镜心堂。”
我点了点头:“纸上之阵终究只是死物,唯有见过那孩子本身,才能判断他到底是被什么牵引着魂魄,‘无影门’究竟是幻象、诱引,还是某种心智外力的介入。”
唐蔓缓缓站起,披风一撩,衣摆轻摆如墨:“我陪你。”
她语气平静,没有多余情绪,却无形中透出那股归雁镇时我最熟悉的坚决。
我轻声一笑:“你如今是东城县的正捕头,亲自陪我走这一趟,不怕被人说闲话?”
唐蔓轻哼一声,微偏了偏头,神色凌然:“命案当前,谁若管得着我,就让他自己去查‘无影门’。”
我低低一笑,站起身来,刚欲整衣出门,她忽然止步,语气低了些:
“还有一事。”
我止步,回身看她。
“有位老僧——空影。”唐蔓沉吟片刻,眉间缓缓压下一道凌线,“你去了镜心堂便知,他确实救了那孩子,也一直未曾离去,日日守在旁边,按理说无懈可击。可我总觉得……”
她缓缓攥紧了披风下的拳指,“他的出现,太巧了。”
“他口口声声说是‘路过’,却恰在出事那一夜登寺,且能一眼识得阵印的源脉,还带有旧时密线的木牌,连镜心堂的何夫人见了他都要拱手致礼。”
我神色微动:“你怀疑他早知此事?”
唐蔓不语,许久才道:“我怀疑……他,或者他背后之人,和那‘门’的存在——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堂中一阵风拂过窗纱,燃香微颤,一缕青烟升腾而起,如幽影横空。
我垂眸看着那烟气缓缓扭曲,脑中不自觉地浮现出那夜伏云寺中,孩子喃喃自语的幻影。
“好。”我缓声应道,“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空影’,究竟是施救的佛者,还是知情的看客。”
唐蔓轻轻点头,负手而立。
门外阳光斜洒,照进搅月楼幽深走廊,我转身唤来随侍吩咐整备马车。心头却隐隐浮出一丝警兆——
若空影并非无意中介入,那这场迷雾之中,便不只是孩童梦魇这般简单。
而是旧影复现,人与非人之间,一场真正的门之较量。
街道如旧,檐角飞霜未化,东都的午阳虽出,却仍带着冬意未消的寒冷。
马车一路西行,车辙压过青石砖,发出规律的辘辘之音。
唐蔓与我并肩而坐,车窗外的街巷景致缓缓后退,仿佛整个东都正沉在一层被灰雾笼罩的静流之中。
“你说,”她打破沉默,语声略低,“这案子,是不是太‘安静’了些?”
我侧过头看她:“安静?”
她拂开窗帘一角,望向外头的街景,语气不带起伏,却藏着警惕:“五个失踪,一个重伤,三个异常死亡。若换做寻常案情,街坊早传得沸反盈天,可你看东都街上,谁在议论?”
我沉吟:“你怀疑……有人压了消息?”
“不是怀疑。”她转头看向我,目光冰冷而清明,“是确定。朝中有人在封此案。”
“若只是一桩失踪案,甚至不需你出手。”我点头,声音也沉了下去,“可一旦触及‘无影门’这个词,那就不是寻常案目了。”
“我查到三桩旧案,都绕不过一处印记。”她取出随身的笔记册子,指着其中一页,“西边谷灵、九溪渡口、黑岩旧村。都是孩童失踪、无血斗却有阵图、目字印,结尾也都写了——‘奏入密中枢,暂封卷宗’。”
“中枢一词,按旧制,即我之所继。”我缓缓道,“可见那时,这已不再是捕司能全权掌控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