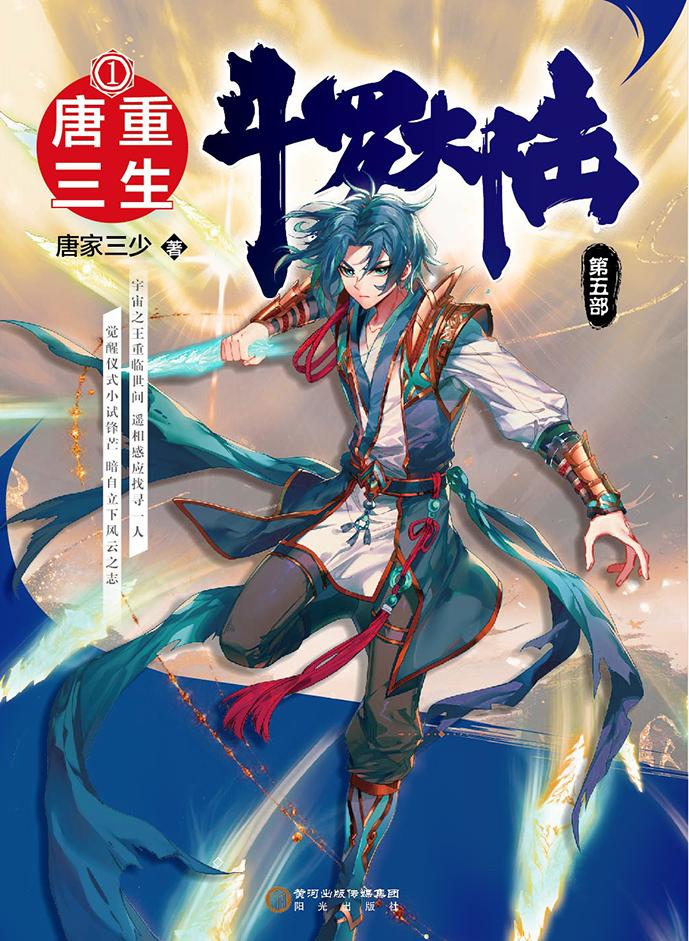BL小说>六州歌头 > 320330(第3页)
320330(第3页)
他解下玉环摩挲一遍,然后递出去,“作为赔罪,你要,我就给你。”
星央说拿就拿,想把中间的石头取下来,但不知怎么嵌进去的,轻易不能取出,只好整个握在手心。
贺今行看着,什么都没说。等他尝试了一阵,想走的时候,就带他一起离开。
竹帘被挑起又落下,垂吊的织穗晃荡不已。傅谨观盯着它们直到停息,才按着胸口埋头弯腰,剧烈地咳嗽起来。
伺候的小厮都鹌鹑似的缩着,不敢上前打扰,更不敢出声相劝。待他咳完自己倒茶喝,看起来没有出事,才询问要不要回屋。
“是该回去了。”傅谨观答。
小厮们便撑起大伞,左右搀扶他行走,余下的则收拾器具,浩浩荡荡回到那座寂静的院子里。
夜雨来得悄无声息。
不知多久,傅景书终于回来,一眼便看到坐在正厅的兄长。
她问守门的侍女:“外面的风这么大,为什么不关门窗?”
那侍女当即跪下。
“开着门,能早一些看到你回来。”傅谨观开口:“也好给你解释。”
傅景书早就接到了禀报,也没有略过此事的打算,“你说,我听着。”
傅谨观便挥退所有下人,“还记得秦王妃的手札吗,他曾经来取,但那时手札已经被裴六带走了。”
“他要手札?”傅景书立即推出一个猜测,脸色一变,“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傅谨观慢慢说:“那本就是秦王妃的东西,母亲为了泄愤,指使人偷来藏匿。我于心有愧,不想再多亏欠。”
他生得早,记事也早。近月来对旧事的记忆却渐渐模糊,已拼凑不出这位长辈的面容,只记得她对他很和善,曾为他治病。
傅景书将自己推到哥哥身边,蹙眉道:“哥哥,我很生气。”
傅谨观抿了抿唇,做出任她责骂的姿态。
但傅景书从未对他说过重话,盯着他半晌,只是问:“你的玉佩呢?”
“也还回去了。”傅谨观说:“你我兄妹和他,不论算不算得上两清,都再无多余的关联。”
这句话很动听,傅景书喟叹:“哥哥能宽心,放他一马就不算全然无用。但是,哥哥要是再这么做,我就不管你了。”
“好,哥哥不会再自作主张。”傅谨观许诺,又问:“今日过去了,之后你打算怎么办?至圣则无情,从他身边人下手是没用的。”
“哥哥了解我,要我出手,就该直接杀了他。”傅景书看到他手边的茶盏空空,伸手贴上茶壶壁,尚有余温。
“刺杀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但是面对一种新的制度新的理念,只杀一个两个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傅谨观停住喘口气,然后笑了一下,“他也不好杀。”
傅景书无谓道:“那就用他们造出的一切,让他们身败名裂。”
妹妹自有主张,傅谨观真心笑道:“好,那我就不担心了。”
他又想咳嗽,幸而及时咬住舌尖才咽下去。这让他知道,他该睡了。
傅景书看着他闭上眼睛,待他平稳入睡,才让明岄把自己推出寝室。
一名黑衣人等候在厅中,向她交代贺今行二人从这里离开候的情况,末了多问一句:“……大少爷眼下这副模样,可要启用统领准备的办法?”
依他暗中所察,大少爷熬得过这个秋天,也熬不过之后的冬天。如统领所言,人没了总得留点骨肉,不为他自己血脉延续,也为大家后路着想。
傅景书面沉如水,“他是只知道育种的畜牲?”
这个“他”指的自然是陈林,但她敢说,黑衣人可不敢附和。
“再让我听到这种话,你也不必再出现在我面前。”傅景书冷冷说罢,唤来纸笔,抬左手写了张字条,“交给王玡天。”
又吩咐:“这些日子陈林不在,除了太后宫中,其他动作都收敛些。”
黑衣人收好字条,“明白。”
太后娘娘要时好时不好的,才能让她在她需要的时候被召进宫。
此人一走,剩下主仆静处半晌,傅二小姐才唤侍女来伺候洗漱。她不想回自己的房间,就歇在次间榻上,和哥哥只隔一道纱帘。
万籁俱寂,惟海棠花状的灯台里外各一盏,烧着幽幽一点烛光。
一盏灯不够亮,贺今行又点了两支蜡烛,让大家的视野更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