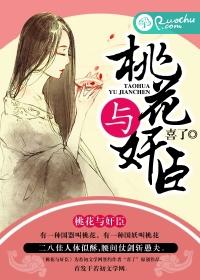BL小说>她执凶刃 > 第二十八章 王爷(第2页)
第二十八章 王爷(第2页)
一旁的平叔一脸欲言又止,老王爷却不理会,只是将手放在了季砚书发顶,一下一下地摸着,什么也不说。
街上传来热闹的叫卖声,甚至有街边孩童跑跳着路过马车旁边,他们的嬉笑声就能顺着那小小的一方车窗飘进来,连带着路边小吃的香气,混杂着街边妇女的脂粉气,一股脑地进到马车里。
“爹。”安静的马车里,季砚书听见自己稚嫩的声音响起,“人这一生,若行至山穷水尽处,该如何呢?”
季桓摸头的动作一顿,他似是没料到年幼的女儿竟会问这样的问题,却也没有急着草草搪塞过去。而是低下头,看向女儿发顶小小的发旋。
季砚书见他久不回话,于是从他怀里爬出来,她梦中第一次直视老王爷的面孔,脸庞轮廓比她印象中的要柔和,眉宇间还有着藏匿不住的潇洒气,与季砚书确实有七八分相似。
老王爷去世时,她还是不知事的年纪,从未有机会与至亲这般谈论解惑过,此时看着季桓,季砚书实在好奇梦中的父王会给她怎样一个答复。
父女对视良久,季桓才开口。
“要走下去。”
他眉眼平静地望向幼女,又重复了一遍:“要走下去。”
季砚书忽然有些急切,她皱眉问:“那若是走不下去呢?”
季桓笑了起来,他微微弯下腰,直到和季砚书视线齐平,才伸出两只手,耐心询问道:“砚书,二人比武,若你一剑已出,而对方动作却比你更快,剑指你面门不到一寸,该怎么办?”
季砚书不明所以:“撤身回挡。”
季桓:“若退无可退呢?”
季砚书:“那就向前。”
季桓点头:“对,向前。”
“侧身向前。或许肩颈和脸侧会不可避免的受伤,但一旦越过这一剑,再向前,便可直指对方咽喉,一击制敌。”
老王爷比划着:“所以有时候当你觉得山穷水尽时,就还要继续咬牙走下去,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才能柳暗花明。如若不明,那便是人事已尽,该听天命了。”
季砚书闭了嘴,此时此刻,她忽然对父亲生出无尽的想念。她有些出神地思考着,如果老王爷仍然在世,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会不会少走很多弯路,是不是不用如此艰辛坎坷,能不能过上她曾经梦寐以求的自由日子?
不能。
她想了想,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像她这样的天字第一号犟种,如果不去摔跟头撞南墙,可能一辈子也长不成现在这副模样。
长宁王府近在眼前,老王爷又将季砚书抱回怀里。季砚书趴在那个宽阔的肩膀上,只觉得头脑昏沉,她甚至分不清这是到底是自己南柯一梦,还是真实存在于脑内的记忆。
直至进了王府的大门,季砚书觉得眼皮越来越沉。老王爷低头看了她一眼,无奈的摇摇头,刚想朝着前厅走去的脚步转了个弯,穿过后院层层叠叠的连廊,将她放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季砚书挣扎着不肯闭眼,却怎么也阻止不了突如其来的困意。季桓就陪坐在床边,不慎熟练的轻拍她的肩膀,大男人动起手来没轻没重的,季砚书觉得疼,却实在是困得说不出话了,勉力张了张嘴,彻底睡了过去。
再醒来时,季砚书觉得恍惚,身上还被一下又一下地轻拍着。她睁开眼一看,坐在她床边的不是别人,正是韩弋。
此时是四更天,韩弋见季砚书醒了,面色一喜,忙凑上前去问:“你渴不渴,要不要喝水?”
季砚书就这么愣愣地看着韩弋,胃里翻江倒海的感觉又一次袭来,可这次她却没任由自己吐出来,而是深吸两口气,缓了又缓,将这感觉压了下去。
喉头腥甜,她哑声开口:“给我端一碗粥来。”
韩弋没听清,季砚书撑起身子凑近,轻又坚定地重复了一遍。
“给我,端一碗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