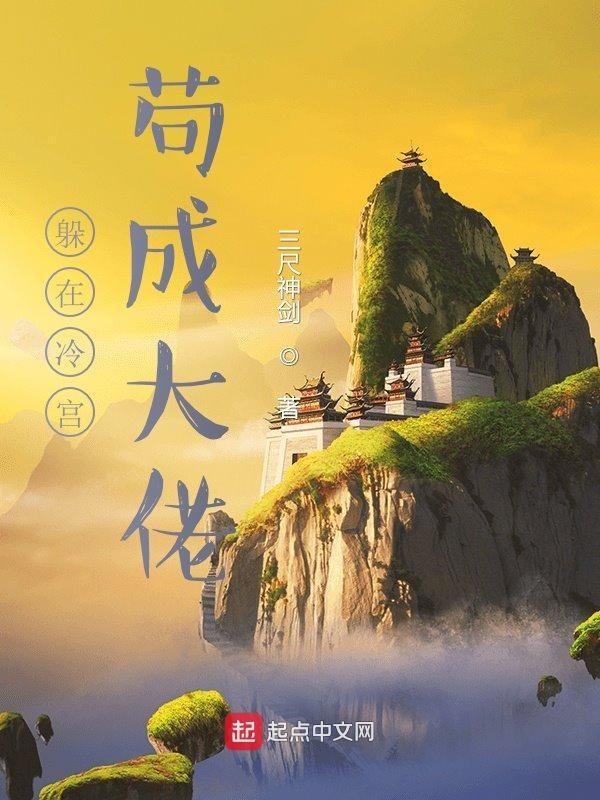BL小说>我和我的淫荡前女友们(回忆录) > 第3章 国庆的狂欢二(第4页)
第3章 国庆的狂欢二(第4页)
有天晚上操完,我们搂着吃鸡蛋,月光从窗子漏进来,照得她奶子泛着光,像两团白玉。
她翻开笔记本,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声音软得像春风,念到“康桥的柔波”时,眼睛亮晶晶的,像在看我。
我打断:“怎么老念这首?林徽因那‘四月天’不念了?”
她脸一红,嗔道:“你就会笑我!‘四月天’太甜,念多了怕你腻……”
她低头,羞得像念错诗,声音细得像蚊子:“这首像你……每次来,闹得我心慌慌,像河波荡来荡去,偏又舍不得你走……”
我心跳得像擂鼓,想:这小骚货拿诗说操她,骚得我鸡巴又硬了。
我亲她一口,说:“你这骚穴比康桥还美,我天天来荡你。”
她羞得捶我,哼唧:“诗都被你弄俗了,徐志摩要气哭了……”
她这话娇得像春雨,文弱得让我恨不得再干一轮。
但她眼角湿漉漉的,像动了情,我搂紧她,低声说:“我哪儿也不走,天天操你到康桥。”
她脸埋在我胸口,呢喃:“嘴坏,心倒甜……我信你。”这灵动的语气,像她改作文时落笔轻点,勾得我心都化了。
每天操完,我们聊些有的没的,像老夫老妻。
她讲《红楼梦》,说林黛玉葬花多伤感,声音软得像勾魂。
我笑说:“你比林黛玉会叫,我操得你不葬花。”
她嗔道:“黛玉要被你气活了,尽糟蹋她!”奶子贴着我,软得我又硬了。
晚上她送我到院子,石榴树下她踮脚亲我,眼睛水汪汪的,软声道:“明天还来陪我写诗吗?”
我捏她屁股,笑说:“小骚货,我不来你骚穴不痒?”
她脸红得像晚霞,啐道:“尽瞎说,我才不稀罕!”但她手指勾我衣角,羞涩里透着留恋。
街上吃面,她吃得嘴角沾汤,我忍不住亲上去。
她缩肩嗔道:“老板盯着呢,丢死人了!”但她腿在我膝盖上蹭,笑得像偷吃蜜的小猫,软声道:“回家再亲,街上我可不依……”这小调皮,比破处那天哭着说“别看”大胆点,仍是她那楚楚可怜的味儿,勾得我夜夜梦她。
国庆最后一天,我们干得最猛。
她骑在我身上,奶子晃得像两团云,骚穴夹得我鸡巴爽得要炸。
她叫得嗓子哑了:“老公……操我……骚穴好爽……”
我抓着她腰,顶得她尖叫:“啊……骚穴要飞了……”
她高潮时身子一僵,爱液涌得床单湿一片,趴在我胸口喘气,呢喃:“你太狠了……骨头都散架了……”
我低声问:“宝贝,这次疼吗?”
她脸颊烫得像火,软声道:“不疼了……麻得像要化了……”羞答答的眼神像谢我,灵动得像抄诗落了彩墨。
我亲她一口,笑说:“小骚货,开学天天操你。”
她羞得埋在我怀里,嗔道:“讨厌,谁说要给你操了!”。
窗外的蝉鸣盖不住她的娇喘,屋里散落的诗本像在为她这浪态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