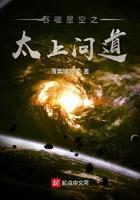BL小说>权臣的掌中莲黑化后 > 辩道(第2页)
辩道(第2页)
惨状比之天水城更甚。
江枝意苦涩道:“若非亲眼所见,焉知京城之外,还有这样的荒城。”
谢徴玄走在她身前,道:“雁门关,乃大黎三座关隘中最为险要之处,历来便是匈奴等族必争之地。战乱,饥荒,百余年之久了。”
“江家军戍守雁门关近一年,没有改观吗?”
“种了粮食,也得春耕秋收。雁门郡百姓众多,要想填饱肚子,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他们是打仗的武将,不是管粮饷民生的知府。”
江枝意涩涩道:“兄……平南将军春时来信,说抽空种了几日稻子,晒脱了好几层皮。不知道秋天丰收时,他吃上没?”
谢徴玄放眼望向北方,沙砾游弋,不见天日。
“走吧。”他快步走过。
不时有衣衫褴褛的老人摊着粗砺的双手追来,却只敢对江枝意喃喃道:“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被天水城流民围堵的景象犹在眼前,她怎敢再胡乱发善心,只能摆着手快步向前。
可老人沟壑纵横的老脸上挂着浊泪,声音沙哑滞涩:“饿啊,饿啊。”
江枝意止步,反复看向谢徴玄并未停滞片刻的背影,终于喊道:“殿下……可不可以?”
谢徴玄回眸,冷漠的眼眸扫过渐渐聚拢的饥民,道:“我不会救你第二次。”
她垂下头,无言跟上谢徴玄。
烽火台上,疾风簌簌,隆冬的风似刮骨刀,寒意料峭。
谢徴玄站在最高处,手指抚过斑驳的砖墙。石砖被风沙摩挲破裂,裂口像一道道干涸的伤疤,无言诉说。他望向远处的重峦叠嶂,枯山寂寥,在风沙中只留下模糊暗影,他眼中愈发寂寥,不知何故。
江枝意想到有关于他登基大典上的传闻,便是在京中最高处的观星台上,他轻飘飘一句话,便将这大黎天下赠予了他的弟弟,也即如今的皇帝。
江枝意小心问道:“殿下为什么不愿意做皇帝呢?”
谢徴玄收回极目远眺的目光,淡然道:“父皇一直抱怨,那皇位宝座太硬。”
江枝意诧异,又觉得好笑,不禁轻笑着问道:“就是这样?”
他轻哼了声,算作回应她胆大包天的嘲笑。
“殿下为什么愿意将我留在身边做事,不怕我误了事么?”
“你那点小聪明,误不了事。”
江枝意撅嘴,并不服气,可终究没胆子与他辩驳,只好悻悻地望向烽火台下,道:“如果我有用不完的金山银山就好了。殿下,如果你当了皇帝,有用不完的钱,你会怎么做?”
他瞥向她,冷漠道:“你的大忌,是太过慈悲。”
江枝意一愣,他竟知道她要钱做什么。
“儒家说人之初性本善,佛学也教人行善积德。殿下却嫌我太过慈悲,我不懂。”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江枝意眉目低垂,看向那些行尸走肉般讨饭的流民。
“殿下是要训诫我,乱世之中,已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时候了。可正如殿下与何慈所言,我被流民伤害,不是因我善,而是他恶。陈谓身死,亦不是因我恶,而是他恶。”
所以,陈谓死,不是她的错;何慈苦,是陈谓行恶的果。她不该为此介怀,但也可秉持初心,为何慈尽绵薄之力。
“善恶之说,只在克己慎独,守心明性。我只认我没有自保的力量,才被人所害,却不认是我善良之过。”她小脸微皱,轻声道。
谢徴玄挑眉,眉目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