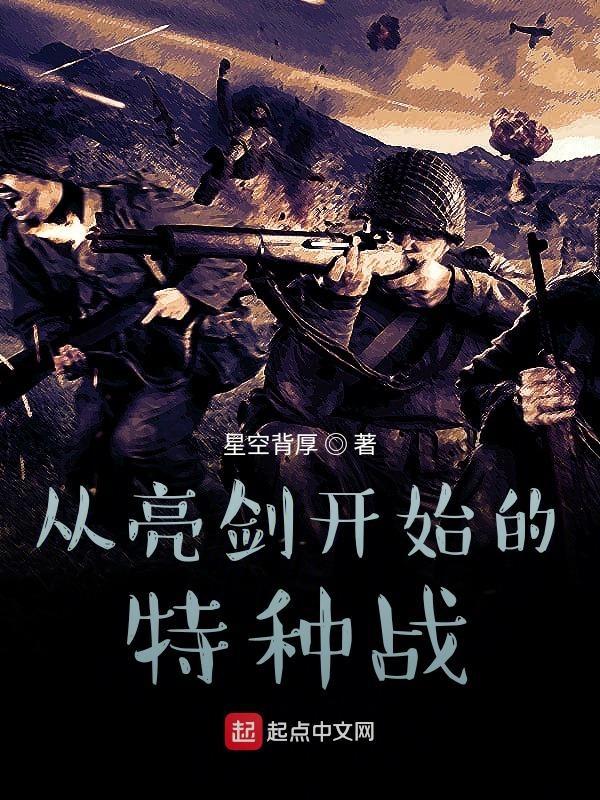BL小说>云雀高飞 > 涟漪(第2页)
涟漪(第2页)
梵云雀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抬起头来一脸不满的看着他。
还没等梵云雀开口质问,黎濯就先解释道:“方才那处隔墙有耳不适宜说话,还请娘娘勿怪。”
说完,给梵云雀赔了个不是。
黎濯是个知轻重,会说话的人精,仅是三言两语,就把把梵云雀哄得没脾气。
“我怎敢怪罪黎大将军?”梵云雀贫了句嘴。
“娘娘怪罪的地方还算少吗?方才不就是。”
黎濯拍拍自己肩上不存在的灰尘,轻飘飘带出一句。
“我那是……”说人坏话被当场抓包,梵云雀定是不会认的,梗着脖子和他叫板:“反正没说你,你就别自作多情了。”
“我自作多情?”听完,黎濯面色一改,突然冷冰冰的来了一句:“那方才娘娘对陛下就是多情滥情了?”
黎濯说的话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怕她对沈轼念念不忘,还残有旧情。
既然二人已达成共识,就得毫无保留的忠于对方,否则他不介意再处掉一个异心者为自己清路。
好端端的,干嘛又扯上沈轼那个扫把星。
回想起刚才在殿内沈轼的所作所为,梵云雀只觉得胸口直犯恶心。
被沈轼吃了豆腐的人还没说什么,他一个大男人倒是不乐意。
莫非他也想体验体验被沈轼搂在怀中作画的场面?
这番景象,光是想想就有够瘆人的,梵云雀也断然不敢在黎濯面前提及。
她抬起一只手在胸口顺了几下,还作出几个干呕的假动作,“快到晚膳的时间了,劳烦黎大将军就别再提一些令人作呕的名字了。”
方才抬手的时候,梵云雀才想起来自己手里还攥着沈轼给自己的画。
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梵云雀在殿内时,甚至没有心思去看沈轼带着她到底画了什么。
她展开已经被揉皱的画纸,只见纸上画了一人在宴席上犹抱琵琶半遮面,其余便无半点值得探究的地方。
“沈轼画了个抱着琵琶的人,这是何意啊?”梵云雀把画纸凑到黎濯面前询问。
黎濯斜着眼偏偏就是不往那上面看,仿佛在于她置气一般。
梵云雀真是觉得脑袋疼,这和自己娶了一个小媳妇儿有什么区别?
说不得骂不得,吵个嘴不出三句,人就要生气,真是满身一股娇贵劲儿。
还是梵云雀先败下阵来。
就当她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吧。
“喂喂喂!”她用手肘戳了戳身旁的倔驴,“你真的不想看一眼吗?”
边说着,还一个劲儿的把画举到黎濯面前,近乎快要贴上人眼珠子了。
黎濯眉间微皱往后一仰,修长的手指捉住梵云雀的手腕,将那画纸给夺了过来。
“没什么意思。”黎濯看了看直截了当的说道。
“没意思?”梵云雀显然是不相信的。
沈轼不可能平白无故的画了这幅画,肯定是在隐喻一些什么。
“哼,不愿意告诉我就算了,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知道。反正画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
黎濯未语,只在心中默默认同的梵云雀的话。
看来她也并非是先前宫人们所传的“绣花枕头一包草。”
结合这几日的所感,梵云雀明显要比他刻板印象里要聪颖许多,且处事临危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