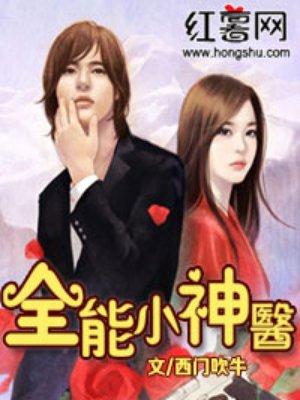BL小说>谁还不是百分百匹配[重生] > 第102章(第8页)
第102章(第8页)
在他洋洋得意,要求第七军团在半路停下,给他沐浴更衣、买衣服买香水甚至做发型的时候……
都是怎么看他呢?
他觉得联络官的话刺耳,怀疑是景佑故意安排他来讽刺自己的,但这话为什么会刺耳呢?
因为人家说的是实话。
他听一听就觉得难受听不下去,瞬间竖起满身尖刺,充满攻击欲望。
……但他又有什么资格呢?
他从未有一刻如此难堪过,高高在上的地位一旦被抽离,他甚至连一个乞丐都比不上,起码乞丐还会在收到钱的时候对给他钱的人说一声谢谢,而他只会吃里扒外。
联络官那几句冷嘲热讽不过是冰山一角,别人对他向来只是表面的阿谀奉承,从来没人看得起他。
他们对他恭敬,只是因为他的姓氏。
然而这个姓氏所有的荣耀,是他记恨了很多年的哥哥带给他的。
明明坐在温暖的室内,景延却好像被丢进了冰天雪地里,多年的仇恨被病寒彻骨的雪水洗涤,脑子越发清醒过来。
景延无意识一个激灵,失手打翻了桌子上摆放的茶杯,茶杯叮铃哐啷滚落在地毯上,茶水沿着桌边滴下,把他的裤子洇湿了一大片。
窗外刮进来的寒风一吹,彻骨的冷。
景佑指尖点了点桌子,唤回景延的神智,“好了小叔,安全署的人到了,准备准备,该出发了。”
景延呆了:“准备……什么?”
“刚刚不是说了吗?终身监|禁啊。”景佑蹙眉看了他一眼,轻飘飘地说。似乎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问,明明刚刚才说了不是吗。
“……你不是在开玩笑?”
“你看我像吗?”景佑扬眉,“难道你觉得,我刚刚是在跟你开玩笑?”
景延僵硬得连呼吸都止住了,颤抖着问:“你真的要关我……我是你叔叔……”
“当然是真的,小叔,”景佑轻柔地回答,说出的话却比拿刀子直接杀人还残忍,“不然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呢?还不是怕您一直挂念赛安利斯,所以特意跟你说一下我的计划,免除你的担忧。”
——这哪里是免除景延的担忧,这压根就是精神凌虐。
景延什么都不在乎,豁出一切想要救赛安利斯,景佑偏偏把赛安利斯拖出来一刀一刀杀给他看,还要告诉他,他不是赛安利斯在乎的唯一的人。
景佑看了眼终端上联络官发来的信息,站起身,掠过呆坐的景延,朝外走去。
景延无意识抬手抓住他的衣角,仰起一张苍白的脸,声线不稳:“你……”
“对了,刚刚差点忘了告诉您了,”景佑看了眼被他抓住的衣摆,停下脚步,俯下身,靠在离他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方,一字一句残忍道,“恭喜您,成功让赛安利斯惹到我了。”
“我本来不想插手这件事的,淮裴不会放过他,他死在谁手里不是死呢,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他这语气实在像死神下达通知,景延被他吓得浑身汗毛不断炸起。
迎着景延恐惧到不断颤栗的眼珠,景佑垂下眼睫,眼梢柔软,语气温和,仿佛在闲聊家常:
“——您想救他是吗?别想了,他死定了。”
话落,他毫不留情抽出景延握住的那截衣摆,毫不留情擦过他往门边走去,转身时带起一阵风,背影笔直挺拔。
临出门时,他回头看了眼景延。
书房采光良好,房间里弥漫着书籍和植物混合的清香,空气中尘埃漂浮,窗户半开,自然寒风不断吹入室内,坐在里面的人脸色惨白,比阳台上冬日开败了的花还要颓废。
“再见了,小叔。”
“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