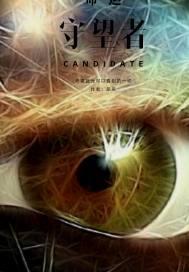BL小说>儒道玄途 > 第二百七十五章 雷震北上(第1页)
第二百七十五章 雷震北上(第1页)
冰冷的雨水拍打在缇骑厂卫的尸体上,顺着他们圆睁的眼窝、僵硬的嘴角滑落,混着尚未凝固的血,渗入脚下的泥土。
那些曾经耀武扬威的飞鱼服,此刻被血污浸透,紧贴在冰冷的皮肉上,早已看不出原本的纹样。
有的尸体被长枪钉在树干上,雨水冲刷着枪杆上的血迹,血滴在了地面的花上将花瓣染成了暗红色;
有的蜷缩在灌木丛中,手指还保持着临死前抓挠的姿势,仿佛想抓住最后一丝生机,却只攥住一把冰冷的泥水。
密林深处,腐叶与泥土的气息混合着浓重的血腥,在雨雾中弥漫。
几只乌鸦被血腥味吸引,落在不远处的枝头,“呱呱”地叫着。
它们歪着头,用黑亮的眼睛盯着地上的尸体,耐心地等待着这场雨停。
很快,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就会成为它们的食粮,成为这片密林的养分。
没有人会记得这些缇骑的名字。他们或许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丈夫,某人的父亲,但在这场乱世的厮杀里,他们的死亡轻如鸿毛。
雨过天晴后,阳光会穿透树叶的缝隙照进来,泥土会慢慢吞噬掉血迹,野草会从尸体旁钻出,疯狂地汲取着养分。
用不了多久,这里只会剩下一些锈蚀的兵器碎片,和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的骸骨,证明曾经有过一场厮杀。
就像这片密林里发生过的无数故事一样,他们会被彻底遗忘。没有墓碑,没有祭奠,甚至不会有人再提起。
只有这无尽的雨水,年复一年地落下,冲刷着一切痕迹,仿佛在说:在这乱世里,死亡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遗忘,才是最终的归宿。
官道上尘土飞扬,四千余人的复仇营如一条黑色长龙,浩浩荡荡向前推进。
步伐踏在地面,发出沉闷而整齐的声响,震得路边的野草微微颤动。
雷震手持长枪,走在队伍最前方。他面色沉凝,眼神锐利如鹰,扫过前方的道路。
他的策略简单直接:主动出击,遇骑便杀。这不是鲁莽,而是看透了局势的果断。
他要的就是以雷霆之势,打散敌人南下的部署,为暗处的青龙帮、烈马帮,还有王晨那六人扫清障碍。
“雷大哥,前面十里就是三岔口,按探马回报,昨晚有一小队缇骑厂卫在那边扎过营。”黄来儿的声音从身侧传来,沉稳中带着少年人少有的冷静。
雷震侧头看了他一眼,眼底闪过一丝欣慰。这孩子变了。经历了那场生死大战,黄来儿脸上的稚气被一层坚韧取代。
从前提起缇骑厂卫,他眼里只有熊熊燃烧的仇恨,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拼个你死我活;
如今,他虽仍握着那柄许泰交给他的短刀,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眼神里却多了几分克制与考量。
方才路过一片密林时,他还低声提醒:“此处地势险要,需提防埋伏。”那份沉稳,已不像个只懂冲动的孩子。
“知道了。”雷震应了一声,扬声道,“弟兄们,前方地势险要,都打起精神来!”
队伍里立刻响起一片低沉的回应,带着压抑已久的怒火。
复仇营的弟兄,哪个身上没有与骑厂卫的血海深仇?
有人的家人被构陷下狱,尸骨无存;有人的店铺被强占,沦为乞丐;有人像黄来儿一样,亲眼看着亲人死于缇骑刀下。
仇恨是他们的铠甲,也是他们的利刃,但此刻,这股恨意被拧成一股绳,化作整齐的步伐与坚定的眼神。
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为了一时痛快而战,而是为了撕开这黑暗,为身后的人铺路。
黄来儿握紧了短刀,指尖触到刀柄上许泰刻下的“守”字。他想起了师傅的眼神,不是恨,而是憾。
那时他不懂,如今跟着雷震一路前行,才慢慢明白:复仇不是目的,守住该守的东西,才是师傅想说的话。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翻涌的情绪,快步跟上雷震的脚步,目光警惕地扫视着两侧的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