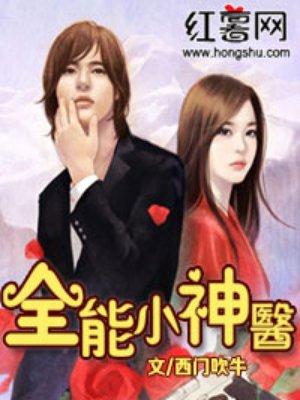BL小说>退后!让老娘扬了这火葬场! > 再见故人修罗场一(第1页)
再见故人修罗场一(第1页)
据回来的朵图说,他们四人还未走到平台,突然下起雨,起先还能维持,后来瓢泼如泄,岩壁湿滑。敖多奎和达因将漆丢弃,也很难维持平衡,两人害怕又紧张,敖多奎一脚踩空,惊慌中把达因也拽了下去,两人一起掉下悬崖,尸骨无存。骆昀徵将她和自己绑在一起,硬生生挺到雨停,她才返回。
“习武之人心智定力确实不一般,放心,你表兄去抓药,过几天就回来。”朵图安慰几句,便随部落里的人去参加葬礼,祭坛不许外人进入。
叶秉荣在一旁摇头,“这就是命,你说头天也没看出第二日会下雨,背时啊。”
于是,送漆之事如此耽搁下来,诃摩谒眉头愈发紧锁。
过几天,叶秉荣又到纾纾面前埋怨:“我都好久没吃上肉了,浑不见油星子便罢,那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绿糊糊是人吃的吗?”他凑上来一脸狡笑道:“你是不是能跟着甸司吃好的?”
她转身从屋里拿出一只糙米饭团,叶秉荣如豺见兔,抢手抓走狼吞虎咽。
他和柯温自到这儿,人瘦了一圈。连她吃的糙米饭团,也时常是诃摩谒让的,庄稼还未到收成之日,崖上的动物越来越少,几乎猎不到什么,许多人家只能撅一些草木茎块或是采择嫩叶树皮。
僰夷人到这儿繁衍近百年,人口慢慢增多,迟早都会走到这步,而不肯下山,就是最大的阻碍。听诃摩谒说,割漆换物这件事也是从他父亲这辈才有的,算是无奈之举,极大缓解了生存压力。但今年为给奶奶买药,向漆宝斋预支的银钱几乎花完,秋收的粮食预计不足,余粮更无,定挨不到明年此时,若食言不送漆,他怕掌柜的不愿再同他做生意。
一处两百余人的小部落尚且时时刻刻有民生之忧,偌大一个国家又何尝止此。亲眼看着诃摩谒整日愁眉不展,纾纾兀地想起岑湜的脸。
不知他的腿伤如何了。
炉上的药滚开,咕噜咕噜直响,纾纾捏着蒲扇,一动不动,眼神呆愣。
“嘶~”一滴药汁飞溅到她手背,烫得人一哆嗦。
将药渣滗掉,她小心翼翼端着碗去寻诃摩谒。
从屋后绕出来,佩珠在骑木马,看到她甜甜叫了声“辛娘子”,纾纾应道:“嗳~”,便踅步走去甸司主屋。
刚转身,佩珠又一叠声叫:“辛娘子!辛娘子!”,语气颇急。许是要展示什么,她笑着想再应,猛回头,一声脆响,陶碗当啷砸在地上,浓郁的药汁飞溅。小女孩儿还在叫她,手直直指着前方。
空地上不知何时多了三个身影。
为首的身材高大,一双柳叶眼顾盼四周后定睛看她。骆昀徵背着竹篓站在他右侧,儒生打扮的男人站在左侧,挎包袱,手里拿着一卷东西。
“莫偃戈?郑大哥?”纾纾胸腔中一阵疾跳,震惶之余,瞬间鼻酸,泪眼模糊。
莫偃戈未说话,将她周身打量后,冷冷道:“你就是如此照顾自己的?”
她不知怎么只想笑,听得出他口中嘲弄之意,却觉心暖。弯腰抓起把尘土抹了抹小腿,将药汁擦去。如今见着他们像见着亲人般,只有欢喜。
“连鞋也不穿了?”莫偃戈浓眉一皱,翻手从骆昀徵的竹篓里扔出一双绣花鞋,“啪嗒”落在她跟前。
纾纾已习惯裸足,走多了便也不觉得疼,叶秉荣说,当按摩穴位也好。
“莫少将军哪里的话。”她笑着揩去脸颊上的泪,深吸口气,道:“我一介民妇,荒野部落里,哪儿有鞋穿,就是买,也买不到啊。这不您来了?”
她捡起鞋对了对鞋尖,尺码正合适。于是略略施礼道:“谢莫少将军,我脏着呢,先收好。”
似有只雀儿在心中飞,她轻巧跳跃,提步上阶。面前的木门吱呀一开,一道巨大影子顷刻笼住她头顶。
一抬头,诃摩谒黑亮的眸子闪着锐芒直刺向她,“你的人来了?”他忽捉住她手臂,隐隐怒意在齿边徘徊,“你终于图穷匕见了?”
纾纾的笑容还滞在脸上,勾起的唇缓缓绷直,又轻启:“什么?”她瞳孔略略一扩,颦眉如川。
哪儿来一阵怪风,诃摩谒脑后的辫子兀地一扬,复落下。
刚擦干泪水的脸,吹得一片冰凉。
“你到底来做什么?”咆哮的斥喝,如滚雷裹挟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