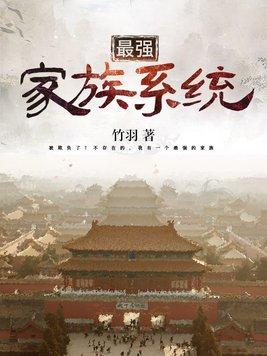BL小说>穿进现场我靠玄学缉凶[无限流] > 130140(第4页)
130140(第4页)
“这条疯母狗当然没有。”周三海叫嚣道:“可是我有。”
几乎话音砸地时,一阵旋风刮过,啪地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扇在周三海的嬉皮笑脸上。
周三海被扇歪了脸,啐出一口血,他揉揉腮帮子,狂暴的怒气瞬间爬上两颊。
他大喊:“谁?自己站出来。”
焦棠揉了揉手腕,这货色脸跟石头似的,足够厚足够硬。
她不耐烦道:“嘴巴放干净点,女同胞也是人。刚才是我打的。没发挥好,不介意的话再来一次。”
周三海阴恻恻看她:“你凭什么打我?你居然敢打我?!”
“为什么不敢?你又不是石神。”焦棠又摸摸手掌心,打一尊石头可能就不是用手了。
“周三海,你有证据证明自己清白就赶紧拿出来。”
周三海又用手指狠狠点了点焦棠,意思大概又是“你给我等着,我弄不死你不姓周。”
这时,周凳对焦棠低声透露:“周三海是登无良的干儿子,打他可以,别打死了,我回去没办法和登无良交代。”
周三海听见周凳的话,扬眉吐气地哼了一句,随后冷脸说:“听清楚了,我昨晚和排子岗的田枣儿在一块。从晚上7点到天明7点,就在一个炕上盖着一条被子!”
方砚用鼻子喷出一声轻蔑,村民们也都用鼻子喷出一阵阵轻蔑。
方砚四处张望:“田枣儿人呢?出来说话!”
村民背后慢吞吞站出来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有一副壮实的身躯,偏偏生了一把玲珑的腰肢,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像田里扬起的麦穗。她的脸庞结实又红润,樱桃小嘴艳滴滴,丹凤眼大而有神。
周凳向焦棠解释:“田枣儿是寡妇,没生养过,她爹娘都死光了,剩她一个,还有一头病恹恹的牛。她就是这样吃上周三海的亏。”
田枣儿往人群前面一站,两双眼睛透着无辜和纯魅。
周三海仿佛心驰荡漾,钳住她的胳膊扯到身旁,威胁:“你和查案的人说,昨晚是不是和我在一起?”
田枣儿有点怵周三海,点了点头。
“说话啊,炕上说不停,下了炕就成哑巴了?”周三海大力摇晃她手臂。
田枣儿吃痛地皱起脸,喊了一声:“在一起,在一起。”
周围传来窃窃笑声,也不知道笑的是什么。
焦棠听得耳朵烦,厉声问她:“是不是实话?”
田枣儿快哭了,连忙应道:“我说的是真话。”
焦棠向尚秋水投去探寻的眼神。尚秋水死死咬着嘴唇,不发一言。
焦棠转头问周凳:“按照乡里规矩,嫌疑人应该怎么处置?”
周凳横杆子一指,指向一间涂了黑漆的门,这处门上挂着“乡大院”三个字。
“长官的办事大院。现在空置着,长官夫人的房间有锁,适合暂时安置嫌疑人。”
目前线索扑朔迷离,当着村民的面,焦棠和其他玩家也不好贸然发动能力,所以她打算先将尚秋水安排在私密的地方,再进行下一步的侦查。
周凳喊来两名小姑娘,给尚秋水捆上绳索,“押送”到乡大院。
焦棠亲眼看着周凳叫人将尚秋水锁在长官夫人的房内门。
走出乡大院,周凳十分得意地拍焦棠肩膀,夸道:“好娃子,你办了一件大案,新长官来了,我要给你记一大功。”
焦棠扯了扯嘴角,只盼着他赶紧走。
周凳忽然扭过半个身子,晦暗不明,笑道:“对了,别忘了今晚要守灵。村里有规矩,死了人,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今晚只能靠你自己了。”
“哦。”
周凳摸着旱烟袋,边走边哼唧:“只盼着别再出岔子。尚秋水是排子岗的人,这次我看方砚还有啥话好说。”
石竹将乡大院绕了一遍,没发现可以逃出去的通道,又绕回焦棠身侧。她实在看不懂形势,犯人一出场就暴露,剩下三天还查什么?
“查一查杨金生的死因。”焦棠突然开口:“既然尸体没办法查清楚,就从死魂入手吧。”
这会儿,游千城和莫笙笛从方砚身边找了借口跑出来。